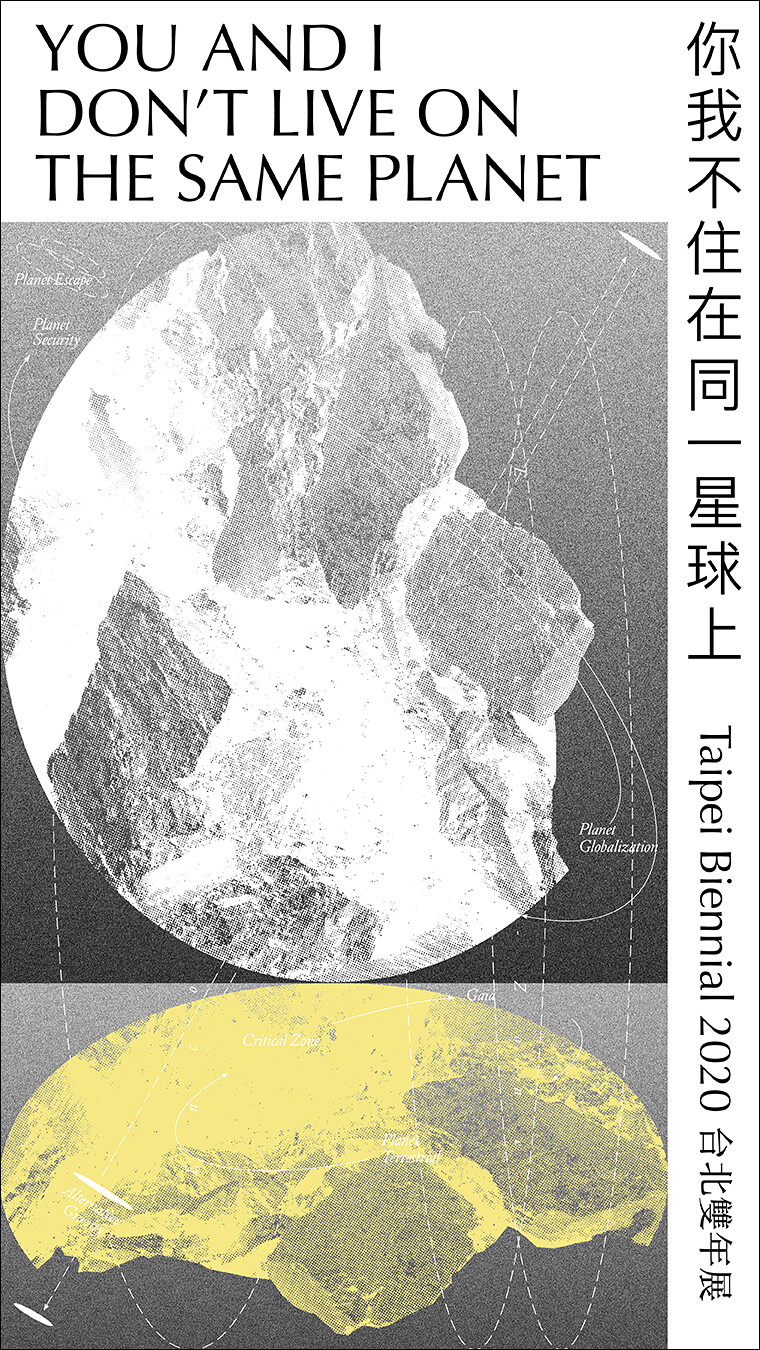給布魯諾
1.
事情是什麼時候開始出錯的?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拋出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事。在此所說的「事情」當然是指「我們這些他者」(nous autres),也就是那些現在我們深知必然難逃一死的文明;早在1919年,深切關注歐洲文明未來的瓦雷里(Valéry)就已哀嘆此一現象,並以複數形式指稱單一的現代歐洲文明。[1]今天,這個單一名詞以愈來愈明顯且令人不安的方式變成一個普世原理——人類物種的技術心靈單一文化(techno-spiritual monoculture)。因為,這個在千百年間以「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自詡的單一形式文明(此處的「單一」〔singular〕同時取其「單數」和「獨一/獨特」兩種意義)可能正處在一個門檻上,一旦跨越過去,就會達成一個不怎麼獨特的「目標」:自我滅絕,而其導因在於它的技術經濟基本結構(techno-economic matrix)與支撐此一結構的宇宙想像體系——換言之就是許煜所謂文明的宇宙技術(cosmotechnics)和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出現了癌化轉移。[2]
卡爾.雅士培(Karl Jaspers)在其名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中提出了「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也就是說,人類物種開始不僅具有一個共同歷史,更共同擁有單一命運之後的時期。[3]雅士培用這個語詞指稱公元前800到前200年間的時代,期間歐亞大陸上出現了孔子、老子、佛陀、瑣羅亞斯德、一群偉大的希伯來先知,以及古希臘諸詩人、歷史學家、哲學家。在那個時期,「今日我們所知的人類誕生成形了。」[4]所有前軸心時代與外軸心時代的文化逐漸被各個軸心文化所吸納,承受消失的痛苦;雅士培相信,在20世紀,碩果僅存的「原始民族」終究會一一步向滅絕。
2.
我們無法在前軸心時代人類的身上找到認同,無論那是指古代或當代的前軸心人類;對我們而言,遠古的偉大帝國都像是另外一個星球。「我們跟華人和印度人的關係比跟古埃及人或巴比倫人要親近得多」;儘管面對這一事實,作者仍舊強調某種「西方特質」。[5]根據他的說法,軸心時代創造了一個法定意義上的普世性「我們」,但只有在「條頓—羅曼諸族」創始的技術—科學現代性中,這個「我們」才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普世概念,「人類真正普世的、星球性的歷史」。[6]
採納雅士培觀點的文化歷史學者之一羅伯.貝拉(Robert Bellah)提出,直到今天,「我們」仍在靠軸心時代留下的遺產生活:
雅士培與莫米里亞諾(Momigliano)認為,軸心時代的人物——孔子、佛陀、希伯來先知們、希臘哲學家們——以一種沒有任何更早期的人物所能及的方式活在當今我們的視野中,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同在。我們的文化版圖,以及在諸多方面仍然定義著我們的一些偉大傳統,都起源於軸心時代。雅士培曾叩問現代性是否代表一個新軸心時代的肇始,但他讓答案維持開放。無論如何,雖然我們已詳盡推敲軸心時代的種種論見,我們並未超脫其範疇,至少目前還沒有。[7](貝拉,2005:73)
以下幾頁的討論所要表達的是,我們懷疑這段思索的最後一句話——「我們並未超脫其範疇,至少目前還沒有」——可能帶有致命性的錯誤,或者該說,只有從悲觀角度詮釋,這句話才能被視為符合真實,因為它似乎讓拉圖(Latour)有充分理由這樣訓誡:「用古早時代的知識處理當前這個時代的各種挑戰,這是無與倫比的智識罪行。」[8]
3.
為利論述,在此不妨接受「歷史上曾發生『軸心時代』」這一論點,或者至少可以承認軸心時代的類型學價值,即便這其中顯然不乏爭議。[9]我們向讀者提出的假設如下: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問世並日益獲得支持的現象顯示,軸心時代遺留的神學—哲學知識已因某些原因而走上退廢一途。如同布洛尼斯拉夫.謝爾金斯基(Bronislaw Szerszinsky)的犀利觀察,基於同樣的因素,軸心時代成了昭告「人類世」到來的「先驅(harbinger)」,而眾所皆知,這個新時代在獲得命名之前早已展開。[10]換個說法,雖然人類世這個時代之所以成為可能,其成形條件之一乃是大約三千年前在歐亞大陸發生的一些文化變異,但人類世的概念,若以此概念昭示出莫斯(Mauss)[11]意義上的「全面性宇宙政治事實」(亦即一場生態災難、一齣經濟悲劇、一個政治威脅,以及宗教騷亂)為考量範圍,顯示我們在使用既有的軸心時代語彙思考那些變異所醞釀的時代時,面臨到極大的困難。因為雅士培的「真正普世」歷史(在此重申,那是一種純粹屬於人類的普世性)已然成為人類世的「負面普世歷史」,[12]其時代名稱無庸置疑地指涉著「今日我們所知的人類」。「人類世」的「人」(ánthrōpos,以下或稱「人類世人」)是在軸心時代誕生成形的人物。
因此,相較於一般針對人類世的導因與形成條件所做的理論思考,我們似乎有必要奮力回溯到更遙遠的時代,直搗軸心變革與各前軸心世界交會的邊界。(附帶一提,許多前軸心世界堅持在世界各地繼續存在,縱使它們遭受一些自命為「人類世人」的使者與日俱增的侵擾。)雖然人類世的各種直接物質導因出現的時間點較為晚近(我們可以將這些導因歸納在「化石資本主義」(fossil capitalism)這個概念下),在醞釀那些客觀條件的智識性可能條件(intellectual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中,或可說是精神條件或主觀條件中,特別是在認為那些客觀條件具有「命定」性質的信念裡,軸心時代確立的人類學架構確實位居核心。[13]
4.
在此沒有餘裕可以評析許多歷史學者所謂「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現象的所有特徵,而其中之一是「突破」這個概念本身,某種與過去之間的徹底斷裂,簡言之就是現代革命概念的雛形(當然這也包括我們所提出的軸心時代遺緒退廢一事)。我們姑且聚焦探討可用來定義「潛藏在所有『軸心』運動基底的共同脈衝」[14]的某些語彙:「跨入普世性的一步」;「人類所具特定人性成份之解放與救贖」(雅士培);「超驗的時代」(the age of transcendence);「對現實的批判性與反思性叩問,以及關於未來演變之新觀點」(史瓦茨〔B. Schwartz〕);「批判的時代」(莫米里亞諾);「縱身躍入存在」;「緊密宇宙經驗的瓦解」(沃格林〔E. Voegelin〕);「第二級思維(second-order thinking)的崛起」(埃卡納〔Y. Elkana〕);「理論性、分析性文化(唐納德〔M. Donald〕、貝拉);「神話權威的否定」(艾森史塔特〔S. Eisenstadt〕);「否定與排除的力量」;軸心時代「反宗教」(counter-religions)的「敵對能量」(阿斯曼);「從內在性(immanence)到超驗性(transcendence)的過渡」(郭榭〔M. Gauchet〕)。最後還須一提的是,我們切莫忘記佛洛伊德繼康德之後,在猶太人破除偶像式的一神論中見到一種「知性的進步」以及韋伯(Weber)提出「世界的除魅(disenchantment)」這個著名觀點,和郭榭與泰勒(C. Taylor)將此概念往回擴充到軸心時代和超驗性反宗教流派的興起(他們將這些流派的出現視為人類文化世俗化過程中的必要步驟)。
5.
我們不難注意到,這些定義看起來很像現代性為自己塑造的形象。它們雖然或多或少帶有矛盾性質(這點在阿斯曼的觀點和他的「摩西區分」(Mosaic distincition)理論中格外明顯),不過本質上是積極的,能在軸心時代中辨認出人類從具有魔幻內在性的原始狀態,受制於與宇宙之間緊密交融的關係、深具自戀色彩的神人同形同性一元論、對過去的盲從,以及社會秩序的神話性凍結等處境,邁向解放(現代性的標誌性關鍵詞)這個漫長征途的最初一步。那種狀態簡單說反映出某種對人類物種「無盡自決潛能」的無知,無論是就其社會政治體制或其否定先天「資賦」的能力而言,甚至可說是一種對此的結構性否定。多數作者顯然帶有演化論偏見,而且他們幾乎一致假定這種「突破」徹底不可逆轉。在最重要的一批「軸心論者」中,數名人士的政治和理論傾向偏向右派而非左派,這或許並非巧合。[15]
6.
這個意識形態星雲的巨大引源當然是「超驗性」(或稱「超越性」),而這個概念反向創造了它的對立體——「內在性」。眾所皆知,超驗的概念是雅士培存在哲學的核心成份;不過在大多數對軸心時代的援引中,這個元素也以各種較不特定的方向被動員運用。超驗性的創造通常被定義為是建立世俗秩序與超世俗秩序之間一種階層分斷狀態,隨之生成本體二元論(ontological dualism)這個所有後軸心時代思維的標誌性特徵。它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當中幾個世紀,種種政治和文化壓力與衝突聚合碰撞所產生的結果,導致世俗秩序在所有面向上一種充滿焦慮的相對化狀態,而這又激發了一套概念性元語言(metalanguage)——批判性反思(critical reflexiveness)、第二級思維——的研擬,並促使人們進行補償性尋覓,設法在超世俗層面同時找到一個絕對基礎和一個救贖願景。於是,自軸心時代以降,人類歷史的標誌性特徵是超驗性的興起;超驗性成為一個超越知覺及/或可理解性的向度,其中蘊藏某種更高超的非顯見真理,並具有一種與個人有關(亞伯拉罕諸教的神)或無關(巴門尼德式存在[16]或現代的「自然」概念)的本質。在軸心變革的某些版本中,超驗性有了時間的形式與秩序(例如基督宗教及由此衍生的許多現代哲學流派),以至於空間足以被視為「異教」(因而違背真理)的極致面向:「空間的真理是時間」(黑格爾)。[17]這種在形而上對空間性的忽視造成重大影響,導致當今我們面對人類世的現象時那種夾雜無能為力與漠不在乎的反應,也就是說,我們似乎沒有能力從「空間的真理」(truth of space)轉移到「空間中的真理」(truth in space)。不過我們拭目以待。[18]
7.
艾倫.斯特萊森(Alan Strathern)不久前發表歷史研究著作《非塵世強權》(Unearthly Powers),他在書中採用的論述出發點是一個明顯衍生自軸心論文獻的二分法,以區別他稱為「內在論」(immanentism)與「超驗論」(transcendentalism)的兩種宗教信仰形式。[19]這部資料非常豐富的專著所探討的問題,亦即導致某些主要超驗論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擴展至全球的政治與宗教因素交互作用,並非此處的關注重點,不過這本書對超驗和內在這些概念的處理方式是啟發筆者撰寫本文的靈感來源之一。
斯特萊森提出三個主要論點,以支持他在《非塵世強權》中所做的歷史分析。第一,站在毫不妥協的「自然主義」立場,他為「內在論是我們的預設宗教模式」這個概念進行辯護,認為內在論的成因是某些「已進化的人類認知特徵」。[20]那是人類物種「自然(天生)文化」(natural culture)的一環、「野性思維」(pensée sauvage)的「本體神學」(ontotheological)時刻。據此推論,內在論本身最初即具內在性;因此,至少在本體論被某些哲學和政治上的反軸心傳統以反身方式重新挪用以前,它一直具有遞迴式的內在性。
第二,由於超驗論具有似是而非的弔詭性和否定生命的特質(尼采會持這種論調),和它與人類心智的基礎代謝之間產生矛盾(這會是斯特萊森的說法),因此它一直是在與內在性的一種不穩定合成狀態中顯現出來,並被迫與後者達成各種妥協。在後軸心時代諸宗教中,這種合成以多種形式實現;舉例而言,它催生出在兩種秩序之間進行調停的各類人物,一些就本體論而言具有曖昧或混種特性的角色:先知、教士、禁慾主義、哲學家、彌賽亞。而基督教的基本教條就是針對軸心分斷而生的雙邊聯繫需求所做的回應之一:上帝或「道」(Logos)[21]的世俗受難化身,最高超驗性的徹底內在化(固有化)表現。「不穩定的宗教合成」這一論題採用施謬爾.艾森史塔特(Shmuel Eisenstadt)的概念,認為軸心時代在已獲確證(已揭示、已宣告)的超驗性與頑固堅持的世俗內在性之間,建立了一種「無可化解的緊蹦狀態」,一種在人類作為生命物種的演進軌跡中固若磐石的基底。
第三,如果我們正確理解斯特萊森的論點,一種如超驗論般「不自然」的宗教信仰形式之所以獲得世界性的成功,原因在於它被政權(國家)這個另具獨立起源的歷史現象所擒獲;國家大力促進宗教真理與政治力量之間的可共量性,作為同盟關係中的一種特有形式,這種可共量性在一神論與帝國之間具選擇性的親近關係(「引人遐思的通聯」[22])中特別明顯。不過,超驗結構與政治體制互相唱和的情形並不侷限於前現代世界;我們不妨思考一下史蒂芬.圖敏(Stephen Toulmin)所分析的17世紀「都會」(cosmopolis)概念,在那個年代的都會願景中,牛頓的自然定律與專制民族國家的治理原則可以並行不悖而互相合理化及合法化。[23]
8.
對雅士培與多數軸心論者而言(這當中當然不包括斯特萊森),超驗性的創造與隨之而來的一切,都是人類必然進程中的環節,是人類多重潛能的開展,使人類在整個自然界中有如鶴立雞群。然而,如《非塵世強權》的論述所重申,一切卻都促使我們明白,沒有任何連續不斷的線性演進是從最初的內在性導向最後(或說終端)的超驗性;隨著超驗論的創新衝動逐漸被內在論的惰性所消蝕,後軸心歷史顯示出的其實是某種交替的節奏,它發生在一種宗教感召力日益破碎、萎縮的例行化過程中,使宗教信仰屢屢陷入各種眾所皆知的病端:偶像崇拜、儀式主義、迷信等盛行於平民階層卻有違時代精神的異教信仰;於是那些創新衝動必須定期獲得改革、苦修、淨化等方面的努力,換言之就是「重新開始」這個古老概念。(這是否意味著,就歷史而言,超驗論的時間之箭路線受制於內在論的時間循環概念?[24])
9.
軸心典範所觸發的超驗性與內在性之辯證,在現代性思維中又有了「自然(Nature)與文化(Culture)之分」這個聖典般的權威形態,而隨著人類世的各種「全面性」宇宙政治意涵逐一浮現,這種眾所皆知(可說惡名昭著)的不穩定性逐漸難以持續。如拉圖在《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中的精采論證,在超驗性述詞與內在性述詞於「自然」(天性)與「文化」(或說「社會」)不同秩序間矛盾的交替擺盪中,這樣的不穩定性格外明顯。[25]有時「文化」成為代表人類超驗性(具有神聖根源的靈魂被現代化或內化為務實理性或象徵秩序〔order of the Symbolic〕的結果)的全新名詞,「自然」則被用來稱呼人類的內在性(人類物種從本能層面到認知層面與生俱來的動物性)。有時「文化」則是內在性的範疇(對世界的開放態度,歷史作為自由的歷史,勇於否定資賦的英雄氣概),而自然天性成為超驗性的範疇(物理與生物合法性的外在與無形特質,歷史作為宇宙的機械性演進)。此外,超驗性與內在性這兩個概念的意義可以相互替換(在前述的定性描述中,我們可以輕易加以掉轉);依據我們所強調的部分是文化之於自然天性的初級內在性,其得以披上海納百川的超驗性外衣(這是一種新超驗主義立場,如斯特萊森針對內在論宗教信仰所持的觀點[26]),抑或是自然天性之於文化的次級內在性,成為一股將意義注入現實的輔助超驗力量(這是一種新內在主義立場)。此種情況源於這兩個概念經常被混淆地使用,有時是讓具有某種心靈或理想秩序的超驗性與具有肉體和物質秩序的內在性產生關聯(如本體超驗性、上天與人間的對立),有時則與此相反,以較為現代的方式讓具有客觀外在特質的超驗性與具有主觀固有特質的內在性產生關聯(如認識論超驗性、事物世界與經驗世界的對立)。[27]我們將自然涵攝文化的情形定性為「主要」,將相反的情況定性為「次要」,因為在現代性中,語言學者會將兩極對立中「無標記」(unmarked)的一端,描述為自然—文化為超越現世的恩典秩序(order of Grace)在世俗世界的弱化繼承者(在前現代世界中,恩典秩序包含現世秩序,不過無法廢除)。這種相對於前現代軸心制度的倒轉,可以用世界「世俗化」(secularization)或「除魅」(disenchantment)的現象加以解釋。
10.
隨著皇權轉移(translatio imperii)[28]建立「自然」這個極的主權,並賦予它凌駕於文化秩序之上的顯著支配優勢,前軸心時期的各種合成型態喪失了它們本已薄弱的平衡;針對此一轉變,後來陸續出現了各種社會—結構主義的回應,但都未能真正動員現代人的情感與心智。超現世(「宗教」)秩序的超驗特質被現世(「科學」)秩序所吸納,將現代的「自然」創造成一個「外部的、統一的、無生氣的、不容置疑的」[29]絕對本體領域。舊有的超自然價值被這種新的、真正的「超級自然」(Super-Nature)強佔了。因此,現代性的基本態勢是阿斯曼對超驗性所做的「摩西區分」漫溢到內在性的領域——內在性於是完全失去它在前軸心世界中曾經擁有,而在後軸心世界中尚能部分保留的特性:它體現「緊密宇宙經驗」(沃格林)與民主普世主義(斯特萊森),它蔑視一神論缺乏包容精神的傾向(後來這種姿態演變成現代人單一自然主義式〔mono-naturalist〕的不包容),它以務實懷疑主義姿態看待「摩西式」信念(阿斯曼),以及被超驗論福音信仰奉為神聖的一些基本二分法,例如體與靈、人(human)與人外(extra-human)、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萬物等。這是超驗性首度出現內在化(immanentization)的情形。這個現象始於十七世紀,亦即「尋找確定性」的時代[30],是對當時不穩定的合成狀態(內在論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懷疑論、哥白尼與伽利略、宗教戰爭)陸續釀成的危機所產生的反應,並在其後數世紀間以不同的方式顯現——從自然天性的領域漫溢到後天文化的領域,影響及於哲學、政治理論及宗教信仰形式的各種趨勢。[31]另一方面,有一個關鍵的變化是,超驗性內在化為自然天性(Nature)的現象以某種形而上的方式將「文化」去領域化(「文化」失去了宗教的基石,成為一種自由浮動的畛域),造成各種強大社會文化力量的解放(liberation)或「去抑制」(disinhibition),[32]而正因為這些力量是「自然」的,意即它們在本體論層面與它們施力的物質環境(地球的能量循環,生物圈)之間具有連續性,結果導致所謂「人類世」的出現。
11.
「自然與文化」這個現代意識形態素(ideologeme)的失敗已經無庸置疑(而且在不只一個意義上可說是「最終」的失敗),這標誌著軸心時代的概念遺緒已然退場。嚴格而言,這個失敗代表人對任何真正的超驗性所懷抱的希望均已告終:沒有什麼「神」或「上帝」會來解救我們。這麼一來,我們是否降格到只能被動接受超驗性的終極內在化,眼看這個世界趾高氣昂地除魅、人類童年的終結(或馬克思觀點中所謂人類的史前時代)——也就是,政治對社會的掌控,技術對這個星球(以及星際)環境實施的主權?或者,面對人類對於蓋婭「在宇宙論意義上的例外狀態」(蓋婭是由它所製造的物質——生命——製造而成的星球)的覺醒,我們應該針對我們的「老舊人類學矩陣」[33]——一種「緊密」的內在性——展開一場反思性的超驗化運動,設法以反軸心手段重新施魅於世界(這必然是一個次級程序,而且帶有一定程度的緊張),對在地宇宙(地球)進行加護治療?然而,有些對超驗性的內在化進行宗教式挪用的做法——例如新五旬節運動(或稱新靈恩運動)追求豐饒富裕的神學理念——極具「人類學層面」的蠱惑力,而貧苦大眾對物質解放斬釘截鐵的訴求更是異常嚴肅的課題。[34]面對這一切,某些諸如「快樂又清醒」(happy sobriety)——這是針對人類將必要性轉換為美德的心理需求所開發的一個極具權威性的公式化教條[35]——這種將內在性超驗化的提案似乎顯得失色無力。一旦我們意識到這點,上述難題就會變得更加棘手。
12.
總結這些討論,我們不妨回到前文援引的黑格爾名言:「空間的真理是時間。」這句話濃縮了歷史哲學的全部意涵。歷史哲學起源於軸心時代,而其在西方的最大成果是基督教及由此衍生散佈的大量文化資產。黑格爾這句話近乎直譯地重現在方濟各教宗的一份綱領文件中絕非巧合,儘管這位教宗極度關切地球起源議題(就定義而言屬於「空間」的議題)。在勸諭著作《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中,方濟各為「和平、正義與博愛」的各種可能性建立了四大基本原則,其中第一個就是:「時間比空間更偉大。」隨後的論述除了教導耐心,還這樣告誡:
優先考量空間意味著一種想要將一切完整保留在現時,並設法掌握所有的權力空間及自我主張空間的瘋狂企圖;這種做法形同讓各種程序凝固結晶,並假定如此能遏止它們的演變。優先考量時間則代表關注程序的啟動,而非對空間的佔有。時間主宰空間。[36]
教宗通諭《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是一份具有極大經濟政治意義的文件,其中可看到另一個敦矚,告誡世人某些偏差作為會威脅到針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所有善意譴責:「我們與環境的關係永遠不能被隔絕在我們與他人及神的關係之外,否則那不過是浪漫的個人主義披上生態環保裝束,將我們鎖入一種令人窒息的內在性。」[37]
因此,時間的優越性成為一種方法,讓「人類世人」得以逃脫被視為牢籠的內在性。[38]雖然方濟各教宗為了讓地球議題成為信徒關注的焦點而付出令人欽佩的努力,但他提倡的「整合生態學」(integral ecology)仍遵守一項絕對教條原則,顧及時間性與超越現世性(extramundanity)之間的救贖關係;這份關係雖就部分程度卻決定性地將人類物種從世間的內在性抽離,使其在宇宙萬物中擁有特出地位。
在歷史哲學論述中,我們會看到這種單方面授予時間的特權,並讓「文明們,我們這些他者」對人類世的宇宙政治挑戰表現得冷漠而盲目。因此,在此重新提出拉圖對這個問題的關切,是相當恰當的事:「這個文明的盲目是否可能部分源於『擁有』歷史哲學這件事?」[39]拉圖用我們當覺得期望大於陳述的語氣做出以下結論:
從前似乎一切事物發生時,彷彿時間中的定向性強大得足以阻斷任何在空間中找到方向的機會。就是這種深層轉變——從一種以歷史為基礎的命運,轉成對於「地理」的探索(這裡的「地理」一詞是因缺乏理想詞彙而將就使用的,其實應該叫「蓋婭地理」)——可供解釋何以任何歷史哲學都顯出某種陳舊過時的性質。歷史性已被空間性吸收;彷彿歷史哲學早已被空間哲學的一種奇特形式所涵攝,而伴隨這種空間哲學的,是地緣政治(其實是「蓋婭政治」)的一種更奇特形式。[40]
軸心時代建立了一種時間性與空間性之間的階層關係,而充斥於西方歷史哲學論述中的基督教末世論則將這個關係「超級超驗化」(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一直是對的)。不過由於地球邊境受到廣泛性(帝國式)以及密集性(榨取主義式)的關閉,這種階層關係正遭逢經驗論層面的挑戰。因此,毫不令人意外地,人類世以科學上最先進的方式重新制定「地球緊密體驗」(在地宇宙、臨界區、以廣義的共生作為生命的真理),而後者需要思想上的「空間轉向」。有鑑於此,前現代及軸心外各民族的原初大地顯得像是拉圖所提的星球性邊界爭端中一個出人意料的另類方案。他所創的「當代性」(Contemporaneity)星球與「在地」(Terrestrial)星球[41]之間的區別,必定是一種時間性的差異,不過那是一種引人遐思的循環時間性,彷彿他在說:「過去尚待到來。」因為「當代性」星球是一直在那裡(也就是說,在這裡)的那個原生、古老、最初的地球;它是政治行動必須能從先前出現的各星球遺留給我們的「毀損星球」回收修復而成的那個「夠好的星球」。
我們剛提到了政治行動。安德斯提議以「沒有神國的啟示」作為現實(Real)無可思考的部分,這個觀點與資本主義「沒有啟示的神國」所隱含的扭曲非現實(unreality),以及基督教和由之衍生的各種烏托邦流派篤信的神話「有神國的啟示」,都大異其趣,然而安德斯的觀點並未提示任何寂靜主義式或宿命論的解決方案。[42]終點的時間(the time of the end)即「世界末日」時間(就空間及地理意義上,希臘語詞eschaton〔末世〕也含有這層意義[43]),這是資本主義宇宙技術組裝體的擴展極限;而就今日而言,時間的終結(the end of time)是生態環境(也就是說,地球空間被賦予的環境)日益加劇的降格與劣化,是一種沒有盡頭的結束。安德斯「總體核戰」的按鈕已被按下,這意味著那個浩劫尚未到來,卻已在數十年前開始。
不再有「等待」這回事,有的只是空間。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的「時機」(kairós)和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當下」(Jetztzeit)所指的,會不會就是「時間變成空間」的時刻?是當時間暫停、歷史爆炸,而人透過行動進入空間的那個時刻?是當無土地所有權的民族從過去到現在依然遭受不接地民族(亦即《面對蓋婭》(Facing Gaia)中的「人類」(Humans)、超驗民族、「我們這些他者」(nous autres)、是我們這些白人,如許多美洲原住民族所說的「Us」的白人)的燒殺擄掠,而為大地奮戰首先意味著加入那些無土地所有權民族的奮鬥的時刻?
因此,作為總結,且讓我們援引巴西亞諾瑪米族印地安人薩滿、政治領袖及族群發言人大維.柯沛納瓦(Davi Kopenawa)的一句話:「白人所稱的未來,對我們而言是一片免於xawara[44]瘟疫的瘴氣危害、緊繫於我們上方的天空!」
Category
Subject
翻譯:徐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