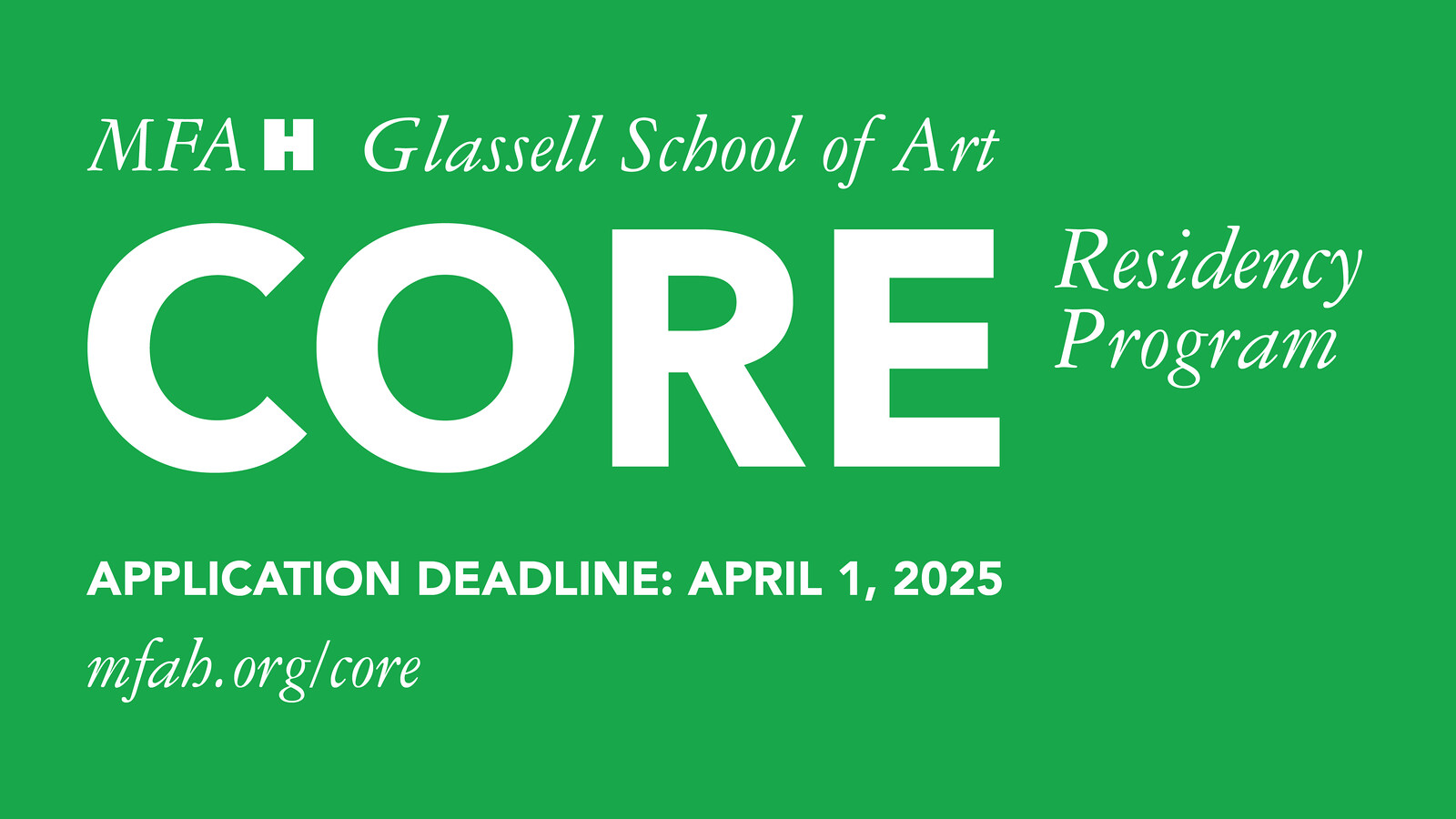胡台麗,《蘭嶼觀點》,1993。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風扯動我的衣袖
雙足陷入沙中
我站在土地觸碰海洋的邊緣
二者交疊
溫柔地會合
在他時他處狂暴衝撞
——葛洛莉雅.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邊境/荒界:新美斯媞莎》(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1987)1
阿席勒.穆班布(Achille Mbembe)主張我們活在一個「脫離民主的時刻」。這個時刻的特色在於它創造「自外於關係的世界」(world outside relation)的狂暴驅力,以高牆和圍籬為區隔,否認行星上的糾纏。2這種割裂規模巨大、又與個人息息相關,甚至可能存在於看似同一陣營之間。如果說,開創新的方式來對抗這股力量是當今迫切的需要,那麼我們可否以某些類型的非虛構影片——它先天是影像製作的關係形式——做為處理的工具?「濱線運動」這個由奎郭利.卡斯特拉(Grégory Castéra)和我共同策展的2020年台北雙年展影片計畫,是對這個巨大問題的小小回應。
對穆班布而言,邊界是「無連結的死亡空間,它否定了共通的人性、否定了我們共享唯一的星球,在這星球上我們因共同境況之無常而連結在一起。」3邊界是民族國家實際的界線,也是更廣泛且無所不在之敵意的概念性標誌。濱線也是一種邊界——但它是不同尋常的邊界。即使濱線在某些方面具有「無連結的死亡空間」的功能,如穆班布説的,是統治當代生活的死因政治邏輯中有危害的一部分,但它的流動和不穩定寓含了不同的觀點,它較接近於葛洛莉亞.安莎杜娃(Gloria Anzaldúa)開創性的作品《邊境/荒界:新美斯媞莎》所談的接觸區(zone of contact)。在安莎杜娃看來,邊界讓二元思維鬆動,由矛盾與曖昧接管,多元的聲音在此衝撞匯合,此單一的地域裡有多重的、彼此牽連的世界並存。這裡是汲取教訓的所在。
多數的邊界強制分隔,而濱線則是以持續協商為特色的閾境(threshold)。它是抵達與離去、安全港口和外敵侵入的所在。根植於在地傳統又受工業發展支配,它是不同人口與環境、土地與水域遭逢的地點。以海岸線為例,潮間帶——退潮時暴露於空氣中、漲潮時被海水淹沒——是週期性變化的中介地帶,多樣性的物種在生態系充滿考驗的變動中尋找共同生存之道。隨著地球變暖、水平面上升,濱線成了最容易受到氣候緊急狀態危害的地區之一。
「濱線運動」處理水陸交界之地的物質環境,也當它是世間生存之不確定和衝突的挑釁隱喻。濱線——這個代表毗鄰、區分、和不止息運動的符號——讓我們在現今的時代,借用馬汀.圭納(Martin Guinard)和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為2020年台北雙年展所設定具挑釁性的題目「你我住在不同的星球上」,去思考共同生存的難題——這是我們要做也必須去做的。透過關注濱線不斷變動的邊界和棲息其中的生物,我們可以學習從生態的角度思考,理解在繁多的行為者之間存在的動態關係,藉以質問它們之間原先推定的區隔狀態。這些動態關係時而和諧,但也可能充斥傾軋和暴力;濱線是看似相互對立的世界無止境進行協商之所在。
「濱線運動」這十八部在1944至2020年製作的非虛構影片,其中多數在最近五年內拍製,它們探索藝術家和影片攝製者如何處理在水濱地區發生的多重交鋒,提出環境危機、本土性、殖民性、和社群的議題。4這些影片在丹尼爾.史帝曼.孟加聶(Daniel Steegmann Mangrané)所設計的空間裡,以如潮水來去的六個循環週期呈現,試圖讓我們理解真實的特殊性和複雜性,以影像和文字做為協助這項任務的不透明媒介。它們透過各種不同策略——從觀察、訪問到推想式的虛構故事到論文形式——在嚴重分裂對立和權力失衡無處不在的情況下,面對打造共享世界的困難和渴望。在傷害與失落之後,它們設想修復與重生的可能性。
「濱線運動」的基本信念是,動態影像可透過真實和想像的方式把人們聚在一起,關注共同關切的對象:即現實本身。關切現實並非要肯定既有世界的美善與完備;相反地,是把建構新世界當成必要的指令。共同的世界是個未來的視界,一個持續進行的方案;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主張,它必須透過不同觀點的交會持續建構。5關注現實並不是為了支撐共識,接受即效性的空想,或相信任何言說是絕對而真確的真理。相對地,它應該是容許持續質問自己的觀點,抗拒自己簡化概念的直覺衝動,對易變的現象保持關注而不滿足於既有。借用另一個圭納和拉圖在2020台北雙年展提出的概念,這是藉由動態影像呈現超越任何個人、但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世界願景,提供上演「外交新碰撞」的可能性。
*
在非虛構電影中討論「碰撞」(encounter)這個概念時,多半它指的是影片製作人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例如法蒂瑪.托賓.羅尼(Fatimah Tobing Rony)在這個脈絡下,認為傳統的民族誌學摒棄了製作「碰撞的歷史紀錄」而接受人類學家是「全知的局內人和一絲不苟的客觀觀察者」的理念。6同樣地,鄭明河(Trinh T, Minh-ha)把碰撞定義為「展示我如何能看見你,你如何能看見我,以及我們兩者如何被看待」,她用開玩笑的語氣點出,這很少出現在「關於『他者』的優秀、嚴肅影片裡」。7非虛構影片製作的歷史充斥著被否認的碰撞、缺乏外交的探掘式研究。這情況也絕非僅限於過去:如今的電影製作人鍾愛的反思姿態,並不足以讓羅尼和鄭明河所強調的問題一夕消失。儘管許多影片製作人凸顯他們對倫理進步的探索,存在於拍片者與對象之間的權力、剝削和自我塑造錯綜複雜的動態迴路始終仍需持續關注。


胡台麗,《蘭嶼觀點》,1993。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濱線運動」的影片建構了對抗、甚至明白質問某些民族誌學傳統否定碰撞的策略。在距離台灣本島四十五海浬外的蘭嶼,胡台麗與一小群人坐在海灘上,在她的影片《蘭嶼觀點》開場她提出了一個問題,直接建立了她的核心關懷:拍攝他者的影像代表什麼意義?她問:「合作拍這部影片有什麼感覺?」一人回答她的提問時說,人類學家在島上的雅美(達悟)原住民族社區參與越多,傷害也更深。胡台麗始終把這個危險性記掛在心,她的影片特點在於它巧妙對抗了民族誌研究工作中暗藏的暴力,思索攝影和權力之間關係、追求本真性的殖民欲望、以及當局者和局外人的界線。在《拉哥斯島》,卡莉瑪.阿莎杜(Karimah Ashadu)用極為不同的方式表達了類似的關切,她使用了她稱之為「攝影輪動機」(camera wheel mechanism)的裝置,以視覺呈現寄居海灘移民的失落無依。當攝影輪經過即將被市府拆除的移民臨時居所,這個拼裝的裝置嘎吱作響,讓我們注意它處於相對位置的凝視,它是內嵌於持續變動的地緣主體的一部分。
電影中碰撞的概念也可以設想成一部影片所代表的衝突和會商。不出意外,水濱區的影像在「濱線運動」頻繁出現。除了地點是在水陸交會處,許多作品也勾勒了不同世界在同一領域碰撞的閾境,捕捉到以對立和衝突為特色的笨重現實。動態影像讓我們看到存在特定情境下的複雜關係糾葛,描繪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不同行為者的交會——不論交會的性質是暴力的、關懷的、轉化的,還是其它。如果說圭納和拉圖用「你我不住在同一個星球上」這句話概述在當代情境下,不同陣營對彼此與生存的物質條件的關係,想法有重大的歧異——嚴重到構成激進性徹底分離的狀態——那麼「濱線運動」則是提醒我們,這種共生的問題並非近代所獨有。帕里西歐.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斯凱.霍平卡(Sky Hopinka)、以及卡洛斯.摩塔(Carlos Motta)的作品展現了對定居殖民主義歷史的顧慮和原住民文化的堅持,提醒我們普世原則(universalism)的宣告往往隱藏在狹隘地方主義(provincialism)之中,強調對隱含於現代化大一統計畫的暴力持續追究的必要性。霍平卡的《馬瑟尼:朝向海、朝向岸》(małni: towards the ocean, towards the shore)(2020)主要以支努干瓦瓦語(Chinuk Wawa)進行,出身聖語族(the Ho-Chunk Nation)的霍平卡在二十多歲時才學習這個近乎消失的,因為貿易而產生的皮欽式傳統語言。親密的對話穿插了對哥倫比亞河流域山川土地抒情詩般的描繪,霍平卡探索文字和電影語言創造世界的能力,肯定電影是開創原住民族未來的載具。


斯凱.霍平卡(Sky Hopinka),《馬瑟尼:朝向海、朝向岸》(małni: towards the ocean, towards the shore),2020。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第二組相互碰撞的世界與土地利用和環境破壞有關,它涉及到群體社區回應政府和企業可能、或已經危害到該群體健康和家園的開發計畫。胡台麗和尤翰.范德庫肯(Johan van der Keuken)捕捉到了反核抗議發生的過程,而碧翠絲.聖地牙哥.慕諾茲(Beatriz Santiago Muñoz)和土本典昭(Tsuchimoto Noriaki)則拍攝了緩慢暴力的後續影響,他們在有顯著比例人口因汙染導致疾病地區——分別是波多黎各的別克斯島和日本的水俁灣——進行紀錄工作。1965年,土本典昭開始了後來成為長期記錄水俁灣及附近地區汞汙染對於政治社會、環境、法律等面向帶來衝擊的工作。在總共十七部的影片中,土本典昭呈現窒素株式會社(Chisso Corporation)所屬化工場排出的含甲基汞廢水如何摧毀海洋生態,並導致食用汙染海產的人嚴重神經病變和死亡。窒素株式會社和當地居民已經不是住在同一個星球上。《不知火海》(The Shiranui Sea)這部在1973年窒素株式會社因業務過失被判定有罪後拍製的影片,探索了這地區的日常生活。土本典昭呈現人與其他非人物種間的相互依存,兩者同樣脆弱易受傷害,但也具備應對災變的堅毅韌性。
電影製作人和世界進行交鋒,同時,影片也捕捉了世界的交鋒。不過,最能夠體現圭納和拉圖的「外交碰撞」的觀點,似乎是第三語境的交鋒:那就是觀眾和世界透過影片做為中介介面而出現的對抗。這是一個與交鋒者的碰撞,在電影製作人和攝影機器的行動和態度導引下與現實建立的關係。在《著陸何處?》(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一書接近末尾,拉圖宣告了如今「創生另類描述」的必要性:他強調,「要建立一個世界秩序,首先要創造一個大致上可分享的世界,透過這個努力來進行評估。」8「濱線運動」的影片暗示了動態影像可用多種方式擔負這項任務,參與部分的評估行動。說它是「部分的」,代表著它有不完全的 (incomplete)、依位置而定(situated)的雙重意義,但不論如何它讓世界變得更可分享而可做為協商暫時的基礎。《不知火海》這類的影片的功能就類似漢娜.鄂蘭桌子的譬喻,用來描述連結和分隔人們共享世界的中介事物,釐清時間來召開對共同關切對象的討論,在影片之內、和銀幕前的觀眾間扮演集會的論壇和多樣觀點的發聲管道。9
「電影是為生者的紀錄」,土本典昭的這句名言說明了他對於他的媒介在生態與關係問題上的理解,它涵蓋了導演的活動、所有在影片中出現的人、以及它所面對的觀眾。這個概念不再把電影視為封閉的虛構故事、或是某位作者(auteur)的作品;在此同時,土本典昭不曾拋棄建構影片的責任,長時間與社區建立互動並且注意標註自己在社區中與他們的關係。如學者亞倫.傑若(Aaron Gerow)解釋,土本典昭的聲明意味著:
不只是電影的主體是生者和他們的環境,同時電影是由生者的作品所定義——這作品基本上是倫理屬性的,涉及到不斷自我反思電影、電影製作人和觀者如何在環境中定義和自我定位,及如何連結到其他的生者。10
《不知火海》是一場大會議,在影片完成後也不會結束,而是透過它在世界的生命延展,觀者根據影片所揭示的複雜生態定位自身的關係,並考量它所描述的世界即是他們生存的世界。與影片的碰撞讓觀者進入與眾多行為者(agents)的關係之中——包括電影製作人、電影機器、所有在片中所再現的人或其他——並隨著現實的認知被開啟甚或重新框架,探索透過接觸轉化的可能。做為生者的作品,紀錄片不只是認證過去的「記述事實的言說」(constative utterance),也是「踐履的言說」(performative utterance),有能力改變它們所描述的現實,觀眾一旦理解自身在共同環境裡的位置,便有可能改變在世界生活的方式。就這層意義來說,世界與觀者透過動態影像的媒介所發生的碰撞是真實的碰撞——它是一種交換、一次的協商——而不僅只是一個單向的傳達。


艾蒂絲.德金特(Edith Dekyndt),《死海繪圖(第一部分)》(Dead Sea Drawings (Part 1)),2010。圖片由藝術家,Kadist Collection,和Galerie Greta Meert 提供。
影片透過形式的運作開啟我們對現實的理解。「濱線運動」的影片雖然彼此不同,卻同樣致力於挑戰主流框架裡被呈現的現實。它們對形式的實驗形成了美學的問題,這裡指的並不是「美化」(aestheticizing)現實——有時它被錯誤地認知為對敗壞的事物搽脂抹粉——而是aisthesis(希臘文「感受」):它要做的是探索我們與世界諸種事物接觸時認知和感官的模態。在《死海繪圖(第一部分)》(Dead Sea Drawings (Part 1))(2010),艾蒂絲.德金特(Edith Dekyndt)取一小張白紙放在水面下,紀錄海水所含礦物質產生轉瞬變化的折射光影。這個簡單的動作顯露清澈空無表面下的充盈飽滿,具有創造細緻、豐富波紋的能力。這是關於水的媒介創生可能的隱喻,它精確捕捉了整個計畫渴望巡遊於透明性(transparency)和提供工具性解釋(instrumental explanation)這兩座危礁之間的慾望,這二者在歷史上構成紀錄片傳統裡——當然也是有例外——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影片所致力並不是完整性和清晰,而是放大間隙、不確定性、迷走的細節、以及對現實的迷惑,以電影的形式讓它們被理解和掌握,以提供集體的思考。
在這場大會合裡頭——影片和觀者、及觀者和觀者彼此的會合——有著達成共識的可能性,但可能有摩擦和迷失方向;encounter(碰撞、交鋒)這個詞在字源上包含了有對抗意思的contra自有其道理。這類外交的碰撞,透過創造對現實可共享的描述,可以重新連結它的觀者感受共同擁有的世界、成為巨大政治共同體裡其中一員——這個共同體拒絕任何起源神話,而是按照埃姆班貝的說法,永遠回到它「始終面對大海的開口」。11

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最黑的海》(The Blackest Sea),2016。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斯凱.霍平卡(Sky Hopinka),《馬瑟尼:朝向海、朝向岸》(małni: towards the ocean, towards the shore),2020。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班.里佛斯(Ben Rivers),《緩慢作用》(Slow Action),2011。圖片由藝術家與LUX,倫敦提供。

土本典昭(Tsuchimoto Noriaki),《不知火海》(The Shiranui Sea (Shiranuikai),1975,2時33分。圖片由Seirinsha製片公司提供。

周滔,《凡洞》,2017。圖片由藝術家與Vitamin Creative Space提供。
佩姬.阿維許(Peggy Ahwesh),《最黑的海》(The Blackest Sea),2016。圖片由藝術家提供。
Gloria Anzaldú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4th ed. (Aunt Lute Books, 2007), 23.
Achille Mbembe, Necropolitic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9), 9 and 40. Emphasis in original.
Mbembe, Necropolitics, 99.
「濱線運動」的週期如下:運動一(2020年11月16日至12月6日):碧翠絲.聖地牙哥.慕諾茲,《黑色海灘 / 力量 / 死者 / 營地》,2016年;土本典昭,《不知火海》,1975年;卡莉瑪.阿莎杜、《拉哥斯島》,2012年。運動二(2020年12月7日至12月27日):潘濤阮,《成為沖積層》,2019年;斯凱.霍平卡,《馬瑟尼:朝向海、朝向岸》,2020年;瑪雅.黛倫,《在陸地》,1944年。運動三(2020年12月28日至2021年1月17日):艾蒂絲.德金特,《死海繪圖》(第一部分),2010年;約書亞.波內塔,《陰陽眼》,2019年;瑞貝卡.美爾斯,《藍色篷幔》,2010年。運動四(2021年1月18日至2021年2月7日):卡洛斯.摩塔,《惡人》,2013年;胡台麗,《蘭嶼觀點》,1993年;帕里西歐.古茲曼,《深海光年》,2015年。運動五(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2月21日):潔西卡.莎拉.林蘭,《伊貝拉-明亮水澤》,2016年;班.里佛斯,《緩慢作用》,2011年;尤翰.范德克肯,《濕地之歌》,1978年。運動六(2021年2月22日至2021年3月14日):佩姬.阿維許,《最黑的海》,2016年;法蘭西斯柯.羅德里奎茲,《鐵月亮》,2017年;周滔,《凡洞》,2017年。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nd e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1998), 52–58.
Fatimah Tobing Rony, The Third Eye: Race, Cinema, and Ethnographic Spectacle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8.
Trinh T. Minh-ha, When the Moon Waxes Red: 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Routledge, 1991), 66.
Bruno Latour, Down to Earth: Politics i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Polity, 2018), 94 and 98. Emphasis in original. (台譯本:《著陸何處?》〔台北:群學,2020〕)。
Arendt, Human Condition, 52.
Aaron Gerow, “Tsuchimoto and Environment in Documentary Film,” in Of Sea and Soil: The Cinema of Tsuchimoto Noriako and Ogawa Shinsuke, ed. Stoffel Debuysere and Elias Grootaers (Sabzian, Courtisane, and CINEMATEK, 2019), 95.
Mbembe, Necropolitics, 15.
Category
Subject
翻譯:謝樹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