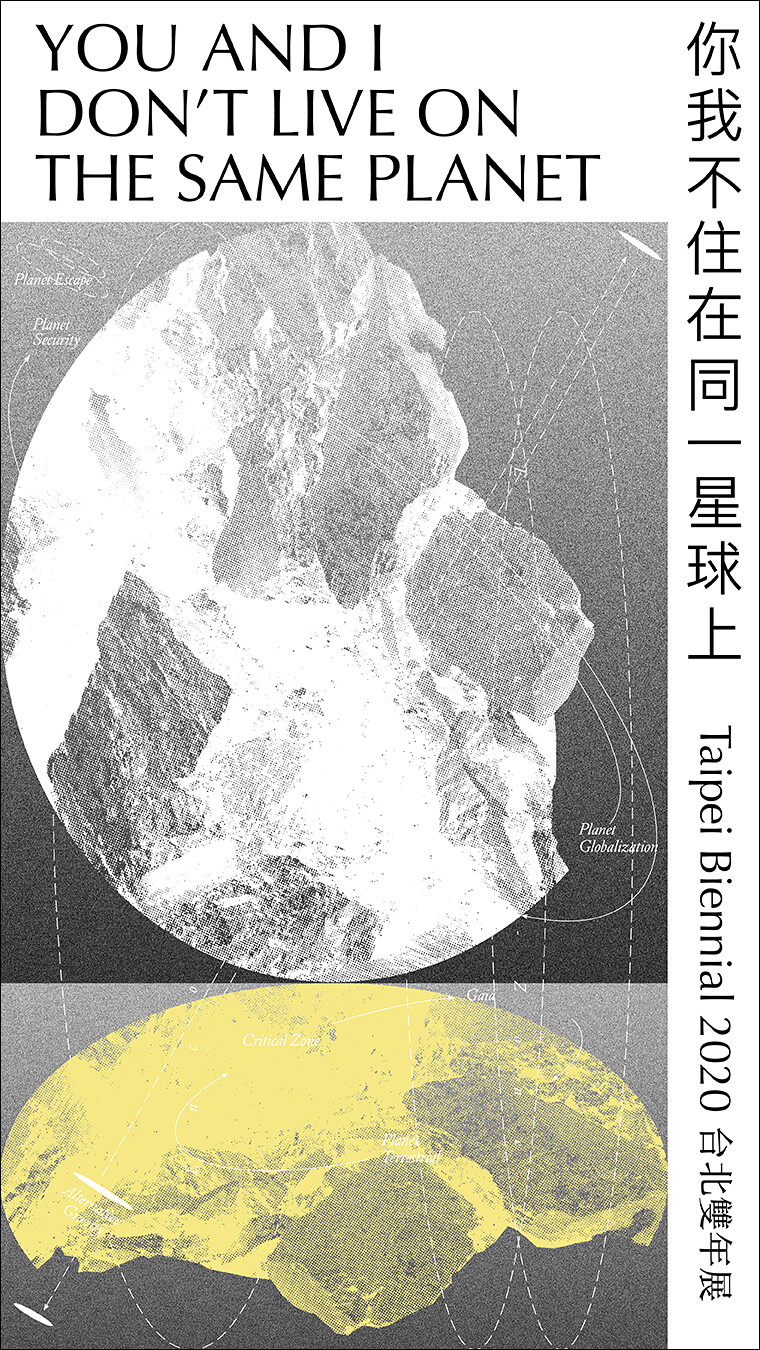今年9月2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宣布了一項溫室氣體減排計畫,預計最遲要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目標。這個有時被視為「世界煙囪」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也是地球上第一工業強國,因此這個國家似乎正走上一條前所未見的發展道路。
計畫發表幾天後,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發表一篇文章,推敲此宣告可能具有的地緣政治意涵。他認為這是國際秩序的一次重大轉折。撇開後續執行成效不論 ,光是中國在經濟、生態和戰略上的份量,恐怕便足以讓此宣告成為阿基米德的槓桿,將深刻地調整當前的工商業政策。但是,這份宣告也意味著集權的生態正在成形,這使得歐洲的生態主義策略急迫地需要重新定位,以提供民主的替代方案一個機會。
歐洲人,尤其是法國人,對於這些宣告顯得很謹慎,甚至還有些沈默。在此,我想試著解釋為什麼歐洲無法搞懂中國此一決策隱含的意義,並說明這種無能為力如何反映出我們這些西方世界的人思考生態的主流方式。
我想強調的第一個重點(亞當.圖茲只隱約指出),即是這具歷史意義的悖論:一個國家竟是透過發動石化裝備裁減計畫展現其政治力量。
自工業社會出現以來,尤其是自二次大戰以降,一個國家調動資源的能力,尤其是調動能源的能力,幾乎等同於它在全球政治舞台上的影響力。煤炭和石油不但是驅動產能的主要力量,產生了高水準的消費力和相對和平的階級關係。它們還是投射跨境戰力的利害關鍵所在,以確保不間斷且低成本的供給。在法西斯主義的插曲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的政治秩序力求穩定(也或許是欠缺真正的和平),它們在生產力的部署中找到一種力大無窮的工具,既能減緩工業社會內部的緊張關係,又能讓這些國家與解殖後的新政治參與者維持既有的關係。
正是這樣的歷史動力解釋了何以大家不願走上生態革命的道路。雖然地球系統科學仔細闡述了氣候問題的迫切性,但發展主義典範的慣性,以及此典範對國際與階級關係造成的外溢效應,癱瘓了轉向綠色的道路。大家確實不斷自問,如果除去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該怎麼才能保衛工業化社會的「社會模式」。至於世界的另一端,人們則尋思如何才能夠滿足發展需求。
中國國家主席的宣告打破了這一邏輯,也因如此這宣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當美國深陷民主危機泥淖、歐洲又抱持觀望態度之時,中國當著這些國家的面,搶先一步打開破口,指出從現在起,國家可以、甚至必須在沒有石化燃料支持的情況下,推行強國政策。因為很明顯地,中國投資低碳生產基礎設施,並不意味著要放棄發展的夢想和地緣戰略的影響力。中國只是宣告,從今以後,它將把國力(包括其經濟動力和戰略基礎)建立在其他可能的素材上。
因此,中國現在的做法可說是一石二鳥。它回應科學,設想一個也許能遏止全球暖化的未來;同時表現出負責任的模樣,維護巴黎協定宣佈的目標,如此鞏固了自身對內及對外的正當性。身為戰爭經濟史家,亞當.圖茲清楚地揭示習近平這一宣告同時具有的現實性與道德性:我們不能再甘願於在爭奪權力導向的自利意圖,以及追求全球共善的純粹意圖之間進行對立的辯論。中國的宣告同時包含了這兩個向度,我們也必須做好準備,因為未來幾年內這二個向度將不斷交纏。
但中國的做法同樣具有政治哲學上的意義,這恐怕也是我們歐洲所缺乏的。我在《豐裕與自由》(Abondance et liberté)一書中提出,在政治領域裡,人的利益總是依賴(多少被視為是)「物力的可能性」。若果如此,便得承認我們正在經歷地緣生態配置的根本轉變。我們長久以來始終在自我質問這個問題:在能源和生態發生翻轉的背景下,一個合法政治權力要怎樣才能長久延續?這亦是如何把資本主義民主化的問題。然而我們現在必須接受一個觀點,即:能源和生態的翻轉反而有利於鞏固權力,讓權力重新合法化。現代政治依賴的物質性正在我們眼前發生關鍵性的翻轉:成形中的後碳政治並不是和平著陸在一個利益共享的世界,而是處於一個政治權力與地球資源調動的新基礎結構、新配置所組成的對抗空間裡。
我想強調的第二個重點則更直接牽涉到存在於西方的氣候與生態運動(紅-綠世界)1。過去幾年,歐洲與美國繼承自勞工運動的傳統社會左派已和生態政治學的政治想像逐漸靠攏。當然,兩個世界在智識上的妥協仍顯得很脆弱,畢竟能否齊頭看待人類的剝削與自然的剝削,恐怕還不無疑義。儘管如此,雙方一種戰略上的協定確實正在成形,參照二戰後的情況,探討經濟干涉主義(dirigisme économique)的復活。不管是相差甚鉅的美國或歐洲版本,儘管規劃的投資方案尚不具挑戰規模,也還未真正以社會正義為目標,但「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已確定是西方左派的共同立場。
然而,「綠色新政」的優勢也是其弱點。此經濟與社會重建方案透過讓能源轉型遵從財富再分配、投資管道控管,甚至就業保障等以突破就業問題的障礙。按此定義,此方案卻可能延續南北間結構性的不平等。因爲,雖然北方國家擁有必要的資源將它們的科學技術資本投注到改造工作,以強化它們的「領導」並增進安全,但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卻將缺乏執行這些方案的資金。這個悖論之所以令社會生態左派更感不安(圖茲最近也曾就此進行解析),正是因為它損害了左派所號召的包容性與全球正義論述。從南方角度看,「綠色新政」常被視為是在鞏固殖民時期榨取主義所獲得的優勢,是發達經濟體應對全球混亂局面的救生艇。
至少從1990年代開始,西方的環境主義就一直受到尖銳的批評,尤其是來自印度的批評。例如,拉姆昌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便揭露對於「荒野」(Wilderness)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想像,讓美國人藉由自然公園洗滌自己的城市與工業內疚感——儘管這些公園是在驅逐原住民人口後才建立起來的。綠色新政的悖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伴隨著富人環境政治的殖民式不安感。生態運動的普遍主義與道德論述,即便加進了社會問題,向來仍與更為陰鬱的現實中,它所要奮力消除的結構與物質上的不平等有著鴻溝。因此我們知道生態學並沒什麼道德上的優越性,它不是安置好的假設條件,而是有待建構的——畢竟和平理念常與殘暴的世界緊緊相連。
在此,中國的決策又再次打亂遊戲規則。因為,習近平並不是基於道德論證宣布擺脫石化燃料,他不是要批判榨取式工業主義對環境的掠奪,也不是想控管或廢除資本主義的剝削體制。他只是想採用一種可稱作生態現代主義的視角,改變物質的基礎,這種做法與權力野心並不衝突。正好因為中國經濟在全球尺度上的重要性,這個由上而下的縱向決定可能會對全球氣候產生正面影響,從而有益全人類(也是在這一點,此計畫不同於例如法國採取的類似計畫)。同時,這項計畫僅是北京所作的全球權力遊戲決策所帶來的橫向結果(一個中國國家主席懂得如何好好操作的把戲)。
在歐洲,我們習慣認為(我自己也一樣)在社會解放運動奄奄一息之刻,生態問題將接棒下去。換句話說,環保主義將重新轉換社會對平等和自由的需求,將之嵌進新的生產和消費體制,從而降低經濟剝削和失範的個人主義的控制。簡而言之,重點在於催生新的社會型態,摒棄高速發展時期的社會型態,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啓動已經停滯不前的民主化和社會包容進程。我們或許可以拿這樣的計畫,判定中國的宣告不夠資格,說它達不到現狀要求,或者說它是靠專制手段解決問題。也許吧。但我們若採取這種策略(我相信這是相關領域的主流思維),我們恐怕無法充分掌握我們正航行在怎麼樣的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水域裡(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從而無法領會我們自身計畫的歷史意義。


美國眾議員歐加修–寇提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為2020年競選活動製作的绿色新政海報。Artist: Gavin Snider; Creative Director: Scott Starrett; Detailer Dayi Tofu, Maria Arenas; Type: Jamie Wilson. Copyright: Tandem, NYC.
我們常把自己身陷的衝突過分單純地想成是兩方對抗,一邊是剝削、異化和榨取性的資本主義,另一邊則是使人與人、人與非人和解的生態政治學。這或許是在紅-綠世界裡,將環境主義的反文化詞彙與社會批判的詞彙混用,才造成生態學與野蠻主義的對立。但我們現在正處於多種道路共存的情境,包括老舊的石化資本主義(正糾纏在它的物質和社會矛盾中)、加速去碳化的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一條更嚴苛、激進的道路,要求我們重新創造進步的意義與生產的社會價值。如果我們同意用這樣(還很粗略)的方式描述當前的情境,那麼歐洲的紅-綠左派便有了不同意涵。因為它不再陷入與資本主義(已被視為不折不扣的化石)的兩方對峙。過去這種對峙將左派化身為進步陣線,並賦予其普世使命。然而目前正開展的中國模式構成了第三項,這第三種發展模式既符合2015年巴黎協議確定的全球氣候目標,但也可能與社會生態運動所捍衛的綠色理念民主有所衝突。
換句話說,生態政治學失去唯一反抗模型的地位:在辯論中,生態政治不再能把自己當成一種反霸權的政治形式。這造成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歐洲的生態政治將與中國模式締結哪種類型的聯盟(至少能保障僅就氣候層面不可或缺的部分),並冒著「把手弄髒」的風險?相對應的問題則是,面對這新典範,歐洲的生態政治將如何彰顯自身的獨特性?
歐洲的社會生態左派必須了解,中國的宣告是否從此體現出一種走出氣候僵局的核心路線,因而可謂「搶盡鋒頭」;或者,在更複雜的三方博弈,其間還涉及與美國的關係下,中國的宣告開啟了一個必須刻不容緩衝進去的破口。這個突破口正是:石化資本主義亦即美式生活發生了根本的弱化(的確,美國在現今的全球政治和經濟舞台上似乎是最弱的一方),從而開啓了中、歐之間更直接的辯論。簡而言之:面對生態岔口,我們應該採取怎麼樣的政治形式? 因此,歐洲的生態運動必須轉向現實主義。這並不意味著它必須加入其他地緣政治行動者既挑釁又好戰的辯論,而是意味著它必須放棄過往用共識化、綏靖甚至是道德化的詞彙做自我表述的壞習慣,同意要在複雜的政治舞台上演出。
畢竟,在社會福利的歷史裡,這個面向一直存在,儘管我們並不願回想這事。社會照護系統的建立始於普魯士,而在某種程度上,習近平有點像是生態運動的俾斯麥:他對環境正義的訴求並沒有興趣,便搶先一步行動,好讓大家閉嘴。若不考慮地緣政治的競賽,便無法理解二戰後歐洲社會權利的進展。這項地緣政治競賽,結合了法西斯主義幽靈、待滅的戰爭、可能發展出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美國的影響。正如英國的一位代表在1952年所言,英國的國民醫療保健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實為閃電戰的副產品。2總之,解放並不總是、甚至主要不是靠寬厚的道德語言達成的。解放也是權力的問題。近年來,列寧的身影似乎在批判思考中重回風采,也許正是因為生態運動還沒有找到它的列寧。
因此,生態運動大可談論戰略、衝突和安全。生態運動可當自己是一種動力,以建立足以承擔權力思考,又不犧牲民主與社會訴求的政治形式。事實上,唯有把這些訴求明確地放到政治的思考與實踐中,才可能實現它們。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放棄過往對道德上去政治化的偏好,因為我們再也沒辦法獨佔對於石化發展典範的批判。新的舞台正在成形,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加入其中。
〔譯註〕生態社會主義
Jan-Werner Müller, Contesting Democracy.
翻譯:陳榮泰(法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