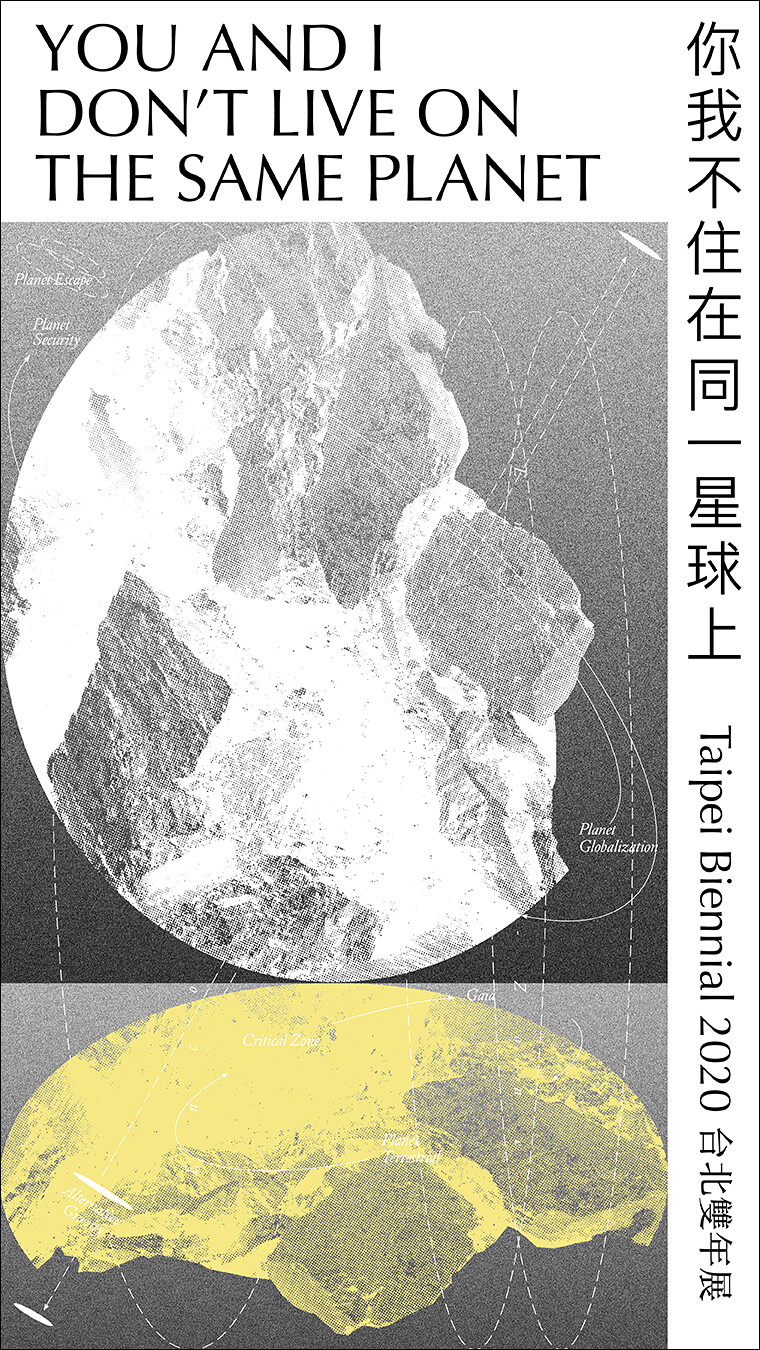人性包括了什麼?更進一步探究,生命呢?是什麼使我們成為道德主體?我們在地球上的宿命為何?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提問似乎只與神學家、形上學家、還有探索存有的哲學家有關。
儘管看來奇怪,如今這些提問都回來了,包括科學家──且正是他們被捲入這些提問之中。此外,因為新冠病毒引起的封城與持續累積的死亡人數,也使得關於末日終結的冥想愈益強烈。
然而,昔日我們要釐清的,在於人類首先是身體或心靈。如今其爭辯則著眼在得知人類是否是物質,且只有物質;抑或,說到底,人類是否只是物理化學過程的一個集合。
如此討論所關注的還包括生命止於何處,在極端時代之生命的未來是何種面貌,而這樣的生命又會在何種條件下終結?
身體、物質與生命是三種區隔明確的概念。人們毋須再依附基督教信仰來理解在人體、在他整個有機體裡,存有某種不僅是物質的東西。而這「某種東西」,根據文化與時代的不同,已有過多種命名。不過,無論文化差異為何,人體的真實(vérité),在於它總是能承受得住一切縮減化約。
而對於人們口中稱之為世界的身體,甚至是它的血肉,這樣的道理亦適用。我們從世界的豐富過剩中,辨識出它的身體。而當下全球所經歷的病毒式爆發,便是這種豐富過剩的典型。
關於這個病毒,很多人的看法是大自然藉此展現其近乎無窮的力量。他們認為這堪稱宇宙級事件,一種未來災難的預兆。對其他人而言,這是打造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之計畫必然會導致的結果,他們且指責現代性推進了這樣的計畫。這個照理來說自由,實際上卻自生自滅且毫無所依的世界,只是讓人類屈服在如今變身為專橫力量的自然的束縛之下。
事實上,上帝的缺席算不上是今日世界的特點。祂那以一種病毒或其他自然災害的暴力形式呈現、劇烈且帶有報復性的存在,亦非我們這個時代顯著的特徵。21世紀初的基本標誌,是在泛靈論裡的擺盪。
結合科技的躍進,資本主義的轉型實際上將會導致雙重過量:Pneuma普紐瑪(氣息)的過量與人造物的過量,將人造物變成普紐瑪(就這個名詞的神學意義而言)1的轉換。而再也沒有比科技數位宇宙成為我們世界的副本、成為普紐瑪的客體化身更能詮釋這種過量。
當代人類的特性,是不斷穿越螢幕並沉浸在影像機器裡,而這些機器同時是夢想機器。這些影像大部分都是會動的,它們亦是各種幻象與幻想的生產者,就從自我生成的幻想開始。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們讓新形態的存在與流通、道成肉身、轉世甚至是復活成為可能。科技不只讓自己成為神學,還成為末世論。
在這個宇宙裡,人們不僅可以自我複製或同時存在於多個場所、多個身體或多個肉身;還可能擁有替身,亦即另一個介於原本的身體與螢幕上主體之身體影像之間的自己。此外,多個螢幕的穿越已成為當代人類的主要活動。它允許我們離開自己的身體邊界,開啟了毫無保護機制地潛入各種平行世界、包括來世。藉由將自己傳輸到螢幕另一端,人類自此可以在與自己保持距離的同時,與自己同在。
此外,當代的泛靈論,更是人類及其與生命之間的關係大幅重組的結果。二次創造的時代因而開啟。自此以後它所牽涉的,是在一個讓人聯想起第一次創造的過程裡,透過技術捕捉生命能量並將之下載到人體。不過這一次,其計畫是將生命各方面的能力,重新安裝在本質上被賦予人類特性的有機人工合成物之中。
這些合成物是為了像人類分身那樣作用。昔日,泛靈論被認為是所謂原始社會裡蒙昧主義的倖存者,當代泛靈論則不但自行操作人工智慧、超級電腦、奈米機器人,亦將人工神經元、無線射頻辨識或腦感應晶片納為己用。
不過,這個二次創造本質上是無神論的。它經歷靈魂出竅、重返肉身以及轉胎換骨等三重過程,在其中重新組構人體,欲使之成為一個混種與共生的載體。這三重過程是帶有聖禮儀式性的,它是諸多科技新宗教的基石。它奪取了大部分基督奧跡的基本類型,好更進一步破壞其穩定性:就從創造本身開始,道成肉身、聖容顯現、復活、升天,甚至是聖餐禮(這是我的身體)。
隨著世界的模控學化(cybernétisation),無論人或神都可被下載到科技物件、互動螢幕、以及實體機器上。這些物件都成為名副其實的鍋爐,而願景與信仰、信念的當代蛻變便在其中錘鍊鍛造。從這個觀點看來,當代科技宗教均是泛靈論的種種表現形式。然古老的泛靈論受生命力原則所支配,而它們受制於人造原則,故兩者間的關係亦是鬆脫的。
因為,在古老泛靈論裡,沒有空氣、水、沒有共同的土地,就沒有身體、沒有生命。比如,在非洲前殖民體系的思想中,生命與身體、還有人類,基本上面對空氣與呼吸、水與火、塵埃與風、樹及其植被、動物與夜晚的世界等都是開放的。在語言的交會點上,一切原本都是活的。這種本質的多孔性成為本質的脆弱。人們思索,在空氣與呼吸的現實裡,人類在地球上的冒險正上演。而唯有創造出生命循環再生的空間,這樣的冒險才得以延續。生命包含一點一滴的完整串連。這是個關乎組構的問題,而不是關乎過量。
作為人類的發源地,非洲或許比地球上其他地區經歷過更多災難性力量。他們因而從中理解到災難向來不是一次完結的事件,並非完成其致命任務並留下廢墟般的世界後就消失。對很多人而言,災難更像是一種始終在進行,持續累積、沉澱的過程。
在這些條件下,從一個較具喘息空間的世界另闢蹊徑,或可成為病毒時代一種新倫理的基礎。因為病毒時代同時是人類世、環境不可逆之轉變、殖民主義以一種前所未見之形式,即科技分子式(techno-moléculaire)殖民主義進行之擴張等所帶來的後果。
粗暴主義(brutalisme)時代,2亦即強行開通的時代,是個夢想機器與災難力量日益成為歷史可見之要角的時代。我們所吸呼的空氣,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灰塵、有毒氣體、物質與排放物、微粒與顆粒,簡言之,各式各樣的揮發物。與其借助沉浸式視覺化技術脫離身體,我們要關注的更是回歸身體,尤其是經由最容易窒息、最容易呼吸困難的器官。
回歸身體,也是回歸到那個地球──不是將之視為一種風土,而是像一個事件,一個最終從根本上挑戰國界的事件。地球是這樣被理解的,它屬於它所有的居民、不分種族、出身、族裔、宗教,甚至是物種。它嘲笑盲目的客體,一如它嘲笑赤裸的獨特性。它提醒我們,每個身體,不管是人或其他,不管多麼獨特,在其身上、本體、在其固有的多孔性中,都帶著記號──不是來自透明可見之普遍性的記號,而是共有性(l’en-commun)與無法計量的種種痕跡。
〔譯註〕Pneuma(普紐瑪),在神學上的意義為精神或靈魂。
〔譯註〕穆班布借用原本指建築風格的Brutalisme一詞(中文將這種建築風格譯為「粗獷主義」,然在此穆班布更強調其暴力),來談日益不人道、失去人性的世界。根據其說法,粗暴主義時代是人類最後一個時代,可加工的人處在一個人造世界的時代,而這個時代的終極計畫在於將人類轉化為物質與能量。
翻譯:陳文瑤(法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