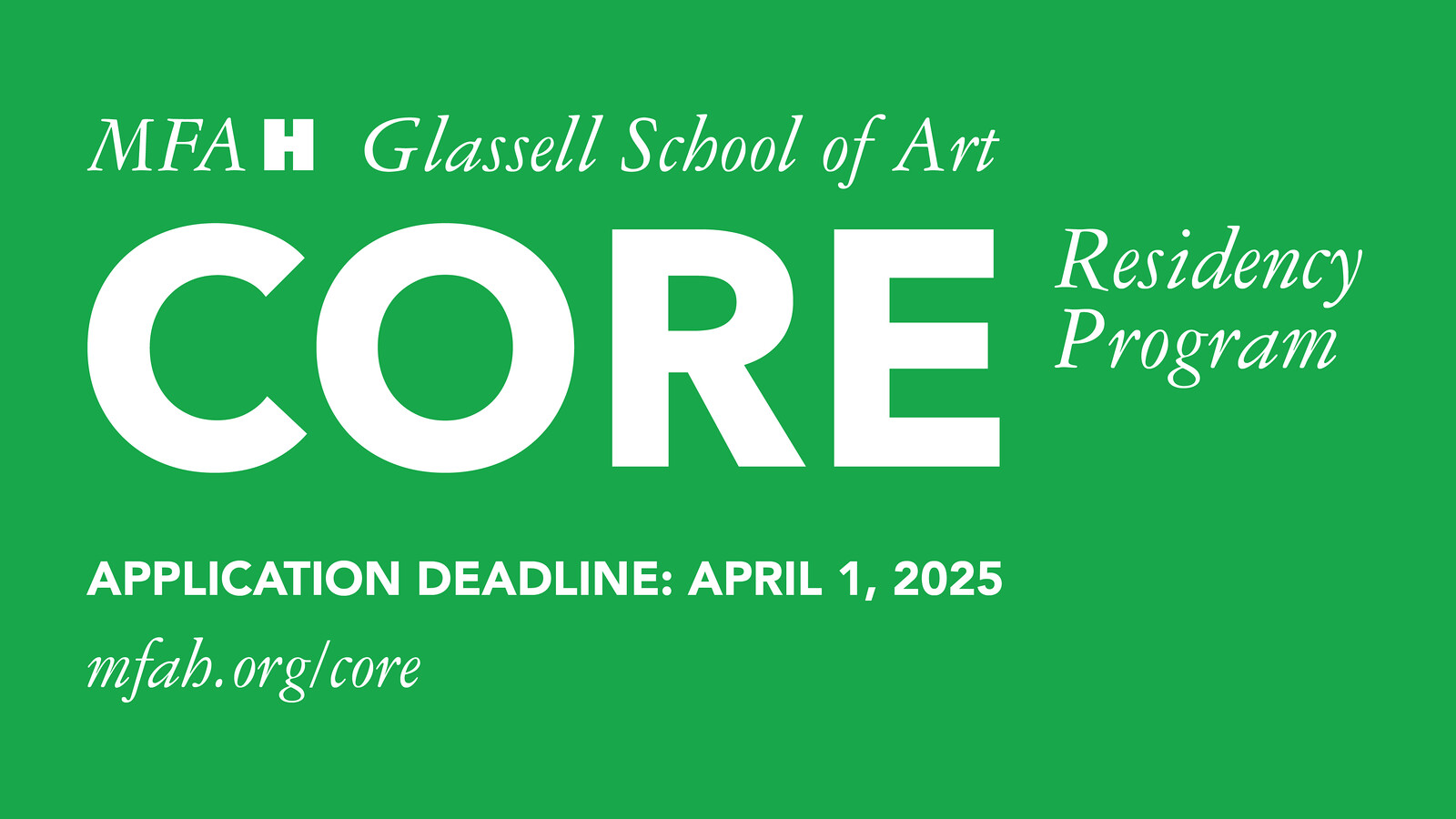我們是分裂的,布魯諾.拉圖如此寫道。也因我們如此分裂,以致於要大家「一起坐下來」討論出某種協議,可謂緣木求魚。這個協議要能在所有情況下有效地讓各關係方承擔起責任義務(obligate),而非只是玩弄文字遊戲──像是至今已經舉辦了二十五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簡稱COP)。我們得責備外交官嗎?要去揭發無效的外交假象嗎?那麼首先便要針對所謂「外交」的涵義達成共識。在我看來,我們需要擴展外交藝術的概念,以應用在各關係方自認於情、於理有義務(obligated)1開戰,否則將違背自我本質之所有狀況。葡萄牙文「Obrigada」的意思是「謝謝你」,英文中的「obliged」也含有感謝的成分。「to be obligated」的意思就是要明白,個體之所以為個體,常是受惠於自身以外的作為。高明的外交手腕,是指能夠換個方式,不需用背叛換取和平而依然得以展現道義的本事──這個概念並非適用於所有狀況,但符合此處在談的內容。我在《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一書中,主張把「責任義務」視為是個人為求歸屬於某個關係者團體而須予以重視之事,且把「必要條件」視為這個團體為求維持下去而對其客觀環境的要求。2責任義務並非行事準則,因為其所隱含的意義,會讓每位成員乃至整個群體陷入三思。而外交官的高明手腕需要這樣的瞻前顧後。
上述主張是有限定性的。比方說,當好戰的一方發動掠奪性戰爭,亦即把對立方定義為獵物時,就沒有外交的空間。將外交簡化成表面工夫、反覆批評所有關係皆以掠奪為目的,並拒絕認同以責任義務為基礎的聯盟,只認定建立在征服和統治上的利益──以上皆非難事。這類評論也許會讓人認為外交是一種非現代化的技藝。我確實也主張,表現出不受任何責任義務束縛的人類,是現代性的產物。3很明顯地,假如這個評論切中要害,我們不但可以告別外交,我甚至還相信,對人類足以捍衛地球上任何值得被稱為「未來」的可能性,也同樣地能說再見。
見識到每屆COP那些參與外交官們的軟弱無能,促使我仔細思考外交演練的適當/不適當狀況(felicitous/infelicitous conditions of the diplomatic exercise)。此處所指的演練不能淪為外交官之間達成的協議,這個前提很重要。每位坐上會議桌的人,都清楚她需要向指派她的權力來源回報,且只有那些權力能承認或否決這個協議。這裡我們不談川普政權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1次締約方會議」所通過的《巴黎協定》,也不談其他國家透過議會制定而成的具體事蹟(parliamentary reification)。讓我們來談談「外交官的回報」應當引起的三思而行模式。在適當的狀況下,這項委託任務背後隱含著條約的接受必須是集體協商出來的,就像外交官的回報對象了解三思是必要的,且須釐清他們需要承擔的責任義務,也意味著與他們可能有所背叛的對象當面協商。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責任義務和違反責任義務的風險,並非懷舊地指涉所謂的傳統民族(traditional peoples)。今日的外交家可以幫我們明確有力地表述使我們分裂的原因,這樣的想法不應該被拋棄,而是需重新整理歸納。
如今,外交失能的環境讓我們越過國家的保護,直接暴露在資本主義下。關於後者,它在實際面上,完全不考慮責任義務的意義和三思而行的經驗。資本主義要求其存在的法律及政治環境要有各式的自由,但它並不負起對任何事物的責任義務,而讓別人承擔其後果。當然,一位老闆可能會三思而行,但一般是出於人性考量,而且就像馬克思清楚看到的,過度三思會讓老闆被競爭對手擠到一邊,也就是說,有一種操作邏輯認為三思就是等著成為掠食者的獵物。
但我們要小心避免落入如此的陷阱,將這種邏輯轉變成全面性或系統性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將得以抵抗這種邏輯的可能性甚至是想像描繪得荒謬可笑。4我認為用來解釋資本主義的方式要夠抽象,才有空間容納當代社運人士呼籲的「我們即自然,自然要自衛(We are not defending nature, we are nature defending itself)。他們的呼籲證實了這種毀滅是可以抵抗的。可以肯定的是,如今那些注定滅絕的無數物種將不會復活,但必須被保衛的,是被資本主義重新定義的世界持續在索求、剝削、瓦解、摧毀的種種。資本主義,正如我將要描述的這樣,是用拆解相依關係(relationships of interdependence)、建立完全無以逃脫的依賴鏈(chains of dependence)的手法,來重新定義人類世界和非人類世界。
那麼,我們應當先用一種積極的方式去理解「我們是分裂的」,朝著造成這個分裂的原因去思考,也就是要想想:是什麼破壞了相依(interdependence)作為一種會起作用的政治效應的想法。這倒不是說,沒有這道分裂我們就必然會團結一致,或出於共同利益去思考。依賴和相依之間的差異無關道德。依賴(dependence)是一種事實,這是首要得認知的。我們的生存仰賴地球的適居性,跳脫這種依賴關係的念頭只會淪為空想。幻想去火星,等於幻想建立一個靠精密複雜的高科技所維持的生活。同樣地,工業化生產的種子,不需土壤即可長成植物,但它們的生命也將依靠農化工業製造的肥料和殺蟲劑來維持。然而自琳恩.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1938年-2011年)之後,生物學家們愈加認知到,如果地球不僅宜居且充滿生命,或是乾荒的岩石化為肥沃的土地,這都要歸因於相依關係的產生。這是一種不會本著無拘無束這樣的想像而建立的關係,因為這些關係所涉及的一切生命體,依著得以載舟覆舟的他者,而有能力完成憑一己之力無法完成的事。這種關係就像我們對於成就自身的助力所懷有的責任義務,是世界各地的人們所讚頌、轉譯、培養的關係。
現代性過程中創造了不斷增長的依賴鏈(而非相依關係),其反映出的,並不是一個自我解放的夢想,即便這個夢想已經誘使好些人發明出了一千零一百種讓自己從「大自然的無常」中解脫的方法。相反地,它反映出的是一種具有軍事意義的動員行動(mobilization)。軍事動員的目標,在於把軍人塑造成只以指揮系統下達的命令為其採取行動之唯一準則的存在體:一支動員起來的軍隊不能因任何事物而有所延遲。這也就是為何動員和對於會破壞紀律與不在考慮範圍內的一切事物麻木不仁,是相互關聯的。因此,當相依關係被依賴鏈取代,就必需為想像築起防衛工事,幻想在沒有摩擦的狀態下仍能持續運作。
根據安清(Anna Tsing)的陳述,十六世紀發明的甘蔗種植園,在成功體現動員模式的同時,也帶來極大的危害,因為這種模式製造出的生命體,既無法建構起物種履歷,也不會進入「易變的」(capricious)附屬關係。5這類種植園的作法是:在不會碰到同種植物或喜好甘蔗的昆蟲的偏遠土地上種植甘蔗(經由無性繁殖長出完全相同的產物);在此之前,要先趕走該片土地上的全部居民,消滅原生植物,然後讓奴隸開始耕種。這些奴隸通常極其短命,造成高度汰換率──就此形成蔗糖、金錢、人的三重循環鏈。
安清特別強調,葡萄牙人發明出的這種農耕模式,等同將土地徹底榨乾,打造一個名為「可擴縮性」(scalability)的理想目標:就是將這樣的生產不失一致性地運作並拓展到最多種區域的能力。安清藉此殘酷地帶出社運人士的口號「我們即自然,自然要自衛」背後的意義。因為今日對可擴縮性的要求,同樣決定了工業生產標準、國家人口管理,和哪些會被認為是可知的、合理的、客觀的。而且,對上述每種狀況來說──雖然每種狀況都依照各自的模式發展──代價都是一樣的,也就是相依關係會被腐蝕、漠視,甚至刻意破壞。因為對於不受各種環境和地方與社會記憶所框限的一般性定義而言,這些關係成了絆腳石。
可擴縮性讓對於「我們即自然,自然要自衛」的理解,不用和「回歸自然」混為一談,或是和狂熱的學術論戰中蓋過思想和感覺的同化作用一概而論:那些論戰竟拿種植園裡悲慘的奴役生活來對照甘蔗的貧瘠!重點不在做比較,而是要指出在迎合可擴縮性的要求時,人類和非人類成本是不可分離的。因此,這種對可擴縮性的需求,讓我們可以找出讓此需求盛行的機構各自的特性。而支持並宣揚這種需求的,除了讓國家和經濟武裝起來的特有理性外,還有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里(Félix Guattari)視為「有王權的」(royal)[footnote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菲力克斯.瓜達里(Félix Guattari)合著,《千高原: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rian Massumi英譯(Athlone出版社,1988),372–74。]的那種科學。面對氣候失序帶來的恐懼,我們都曾聽過一個可被廣泛應用的最佳警語:每人都必須減少「個人」的碳足跡。
然而,依賴鏈本身脆弱且衝突不斷。它們顯然是專橫的,且要求我們忽視它們認定無足輕重的事物,但它們無權讓我們遺忘。每一條鏈都可構建出一種根除依賴性的意圖,但在實驗室、法庭、醫院,和所有其他它可以決定何者重要與否的地方,它想排除的事物仍堅持存在且進行反抗。每一條鏈都有它的位置,可以被評估、批判、甚至公開挑戰。約翰.杜威(John Dewey)便是從此中拉出與公眾的出現的關聯性:這是對於讓國家視為不具利益而加以忽略的對象遭受傷害的權力所衍生的抗議。
一旦這些鏈彼此牽連,便會被注入在個別狀態時不會擁有的力量,一種可以創造出各種依賴性(dependences)的力量,這些依賴性會化為無以避免的必需品,將顧慮與三思的可能性一筆勾銷,讓所有抗議噤聲。糖過去曾作為奢侈品,如今已演變為生活必需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從什麼立場關心甘蔗種植園的議題呢?又有誰能洞悉他人為這種充裕的供給所付出的代價,以及為了維持這種生產模式所牽涉到的軍事、法律、商業機制間的勾結?相對於人類族群所推崇,且感受到甚而培養出責任義務的交錯糾纏的相依性,鏈與鏈之間被綁住的互連性,創造出一種沒有著根的網絡,將每個鏈引發的麻痺效應集中在一起,建造出讓抗議者繞得團團轉的迷宮,而且,如同我們今日已察覺到的,大放厥詞並不會受懲罰:「你們都認為控制石油開採就能拯救地球嗎?你們會觸發金融風暴……」
我將資本主義描述成一種以複雜的依賴鏈網絡取代相互依存關係的力量,其意義在此有了充分的展現。資本主義並非操控國家、科學或經濟的幕後黑手,它為了把依賴鏈連結起來,並且要讓依賴性變成不可逆,從未停止利用國家、科學、經濟各自的抽象概念,並藉此創造出「極惡的選擇」,以在面對災難席捲而來的當下,徒留下分裂且無力的我們。
然而要記得的是,可擴縮性需要長久的維護。它並不保證永遠居於征服者地位,即便是已被根絕的相依性仍會不斷地復甦。這樣的復甦並非「本質良善」──沒有什麼是「本質良善」的。所以我們要談的既非「大自然拿回它的權力」,也非人類聯合起來反對被奴役,因為這些畫面充滿了被可擴縮性綁架的想像──一個對巨大的真理之力降臨以徹底消除任何束縛它的力量的幻想。無論是英勇戰爭的史詩場面,或是懺悔與救贖,都不在討論之列,而就時間點來說,也不適合討論外交。外交實際上需要的──一個團體思索其責任義務制定方法的能力,以及這個團體為維持它的以及它必須維持的事物整理出通用道理之能力──正是被依賴鏈摧毀的,削減為一個空洞、哀傷的想像,一個反覆無常的慾望,一個被連根拔起的意志。今日的外交家並不具備養成他們所需倚賴的協商手腕的條件。
要重新活化相互依存的觀念,我們不需指望外交家,而是杜威提到的探究者(the inquirer)。杜威的探究者並不製造中立的知識,讓分裂和無力感擁有立足的依據。他們是實驗者,就像所有進行實驗的人們那般積極介入,但不是在實驗室,也不是為了瞭解如何從其實驗對象取得可靠知識。當今探究者的目標,應該是去學習轉化那些在體驗的人和他們所體驗的事物之間的關係,而藉此重新活化對相依性的感受。
相依性的感受並非衍生自知識。首先,它是一種「讓自己被感動」的行為,且包含既非主觀也非客觀的感謝之情,因為它的真實性存在於其生成性(generativity)。如果這種感覺需要被培養,那是因為它很脆弱。身為人類的我們再明白不過,我們有可能在自己周圍築起壕溝,隔絕對於成就自身的種種外力的感謝之情,讓自己落入忘恩負義的境地。然而,無論相依性是多麼罕見、脆弱,或只存在夾縫間,探究者的任務是要使其成為某種實際的、政治的想像,讓它一點點,一步步地重新活化。許多社運人士將這種重新活化稱為「復歸」(reclaiming),且瞭解這不只攸關再生,也關乎戰鬥。因為那樣的再生發生在險惡的環境裡,有可能攫取且束縛住任何單純善意的初衷。
讓相依性重新回歸並作為預設條件的再活化做法需要培植,播種的工作可以交給探究者來執行,但種子的成長茁壯則需須靠土壤的養分。意味著這些做法將需要拒絕可擴縮性的要求,並創造自己的土壤,是一種製造我們可以稱作在地(vernacular)的共有意義的方法,因為其用字遣詞都紮根在這塊土地上。這也意味著,以復歸之名的奮鬥,應該抗拒以一個可用等級或程度表示的意義來界定它所代表的事物,讓它為所編織出且深陷其中的各種感受模式的糾結,承擔起責任。
在這種責任感再次具有意義之處,外交家便可以重新主張其地位的實質意義。因為相依性的培育再度興起,顯然不足夠為學習面對鄰近、重疊、尚待建立的關係、放手一搏的信任、要被轉化為生成式記憶的哀傷等種種問題提供解答,卻是共同成長的開始。被點名加入「我們即自然,自然要自衛」的「我們」當中,肯定會包含以不同方式承擔義務責任的少數群體6──農民(peasants),以及抗拒可擴縮性的規則,拆毀他們過去為了把虛幻的、傳聞的、不合理的排拒在外而築起的壕溝,而學到重新主張其義務含意的其他群體,像是研究人員、科學家、醫者、技術人員、法律從業人士、護理師、有信仰的人,當然還有被殖民者的後代。
外交家在這種環境下如魚得水,因為他們會介入有不同責任義務的各方之間──儘管相關各方還是會表現出能夠對自己如何制定自己的義務提出質問,能夠一起三思,也就是能夠抵制多數人想將歧異轉變為對立的夢想。於是,外交協議就能拼裝出部分的連結,就像所有方言之間的溝通。這種協議無法保證能留住原始的純正性,但如果成功了,就能用各自成立又互相關聯的方式,創造出描述已被學習的、讓相關各方成長的故事和說法。這就會是外交家要傳達的──不是模式或論點,而是想像的催化劑,是把重新發明闡述問題的方式加以升級的動機,不受可被規模化的、國家強制的命令所限。
我們是否能想像有這樣一個國家:它能接受其地位和責任唯有在預設情況下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其地位和責任是臨時性的,因為重新發明問題的新方法還未接受過測試?
這個國家很清楚光靠一己之力無法摧毀癱瘓它的依賴鏈網絡,但它能否給學習一環接著一環地拆解這個依賴鍊網絡的人們一個機會?這個國家知道當我們的世界和想像在重新生成的時候,該如何把空間釋放出來?我們會不會需要大膽假設這個國家厭倦了假裝,在面對自己的無能為力時不知所措;堅信一旦它放手,亂世便會降臨?或許到時我們應該發明療癒者,用來對付那些相信自己是公眾秩序堡壘的人們,教導他們如何感激新的發明,如何理解在沒有他們的幫助之下完成的事,並不全然是要用來對抗他們,只要他們能證明自己值得我們的信任。
在我的《宇宙政治,第二卷》(2011年出版)中有提到這個概念。.
伊莎貝爾.斯丹格絲(Isabelle Stengers),《宇宙政治,第一卷》, Robert Bononno英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2010)。
若欲進一步了解約定和責任義務在遺世部落的生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我推薦Michael Asch的佳作《On Being Here to Stay: Treaties and Aboriginal Rights in Canada》(多倫多大學出版社,2014)。
參見Philippe Pignarre與Isabelle Stengers合著,《Capitalist Sorcery: Breaking the Spell》, Andrew Goffey英譯(Palgrave Macmillan,2011)。
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末日松茸》(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5)。
此處的少數群體要以德勒茲和瓜達里發展出的概念來理解(《千高原》,頁291),意指使其脫離多數群體的無名規範的生成過程。
翻譯:沈怡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