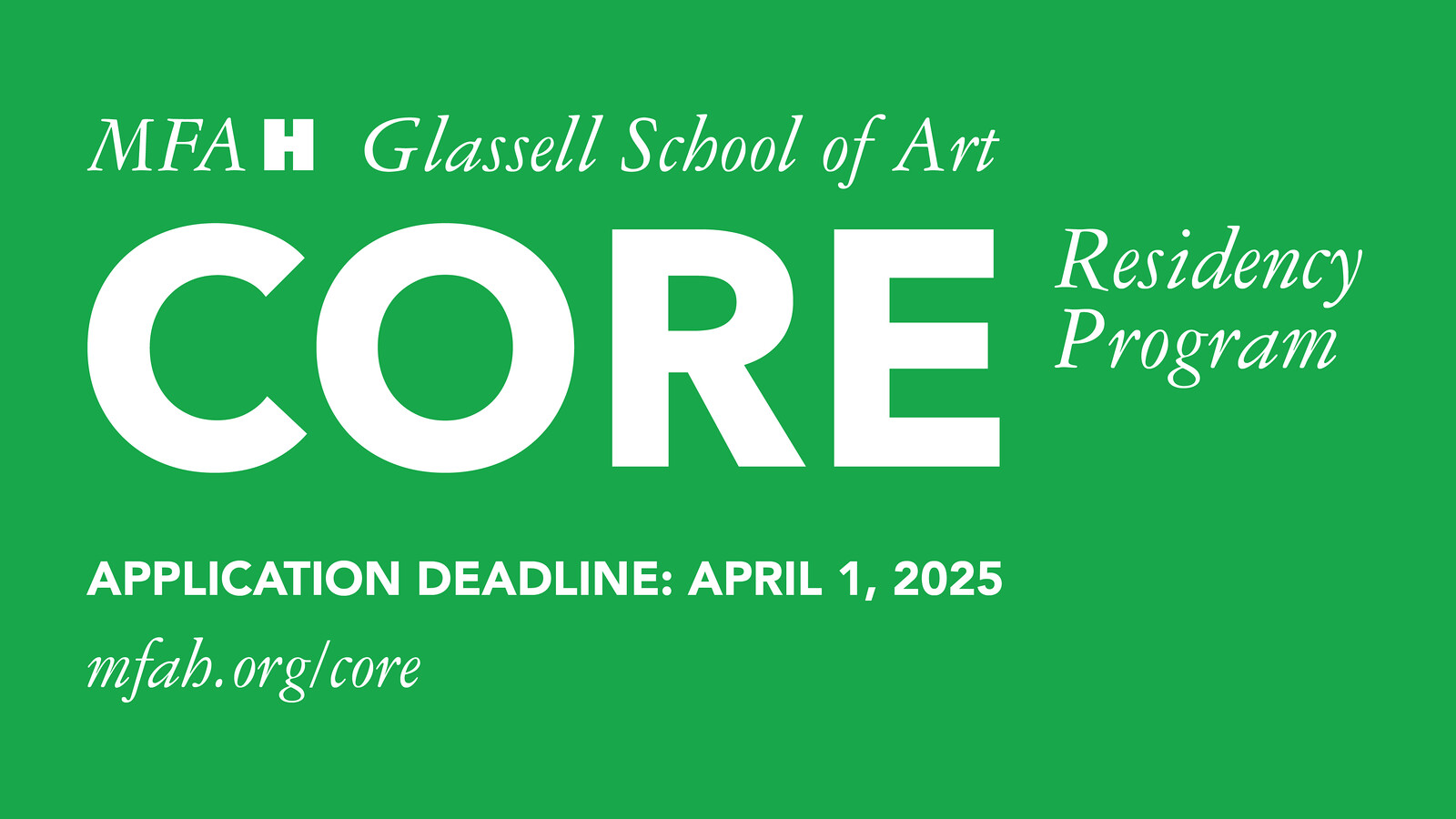一位藝術家對《巨獸行星》的演繹。一個巨大如彗星般的氫雲,從溫暖的、海王星大小的行星上滲出,另描繪了其母星GJ436,一顆暗淡的紅矮星。圖片來源:NASA、ESA和G. Bacon(STScI)。
一、行星生活的質心
我們可以像一座行星般生活嗎?抑或,行星可以像我們般生活嗎?
人應該過怎樣的生活,是社會理論中的核心問題,涉及存有論、知識論、政治和倫理等向度的思考。而一座行星應該過怎樣的生活,看似涉及文學擬人化,實則觸及行星的意義。行星(planet)一詞的希臘字根就是流浪者(wanderer)的意思,曾被用來指涉太陽、月亮、金星等似乎環繞我們的天體,至少從人類的體現觀點來看。我們自以為生活在穩定的居所,把間歇性的天搖地動視為天譴。我們相信大地是宇宙的中心,恰如肉身是我們在生活世界中進行各種感官功能的核心。即便在科學證實大地乃是環繞著太陽,我們依然只能從棲居大地上的肉身去碰觸世界。然而,嚴格說起來,地球並不是繞著太陽轉。太陽系中的所有天體,包括太陽,都繞著總質量的核心在轉,亦即質心(barycenter)。質心並不是固定的,其定位取決於系統中的行星在軌道上走到哪裡。即便是系統中最大的天體,太陽,也不得不受到每一顆行星和無數其他物體的牽引,尤其是最大的木星。同樣地,月亮也不是繞著地球轉,而是月亮和地球一起繞著這個系統的質心在運行。1
我們生活在地球行星上的質心是什麼?我們並不會像天體般繞著一個隱形的質量核心轉動。但或許,我們確實以其他的方式在環繞彼此。正如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的蓋婭假說所隱含,我們的環繞彼此並不僅是隱喻,而是關於地球上生命複雜的生物化學演化。2
我們不僅環繞彼此,我們還包裹著彼此,形構出新的生命形式。此處的我們,毫無疑問不僅是人類,而早已經是跨物種的雜揉體,在身為人類物種或個體之內與之外的界線中。馬古利斯在1967年備受爭議的論文中主張,粒線體、葉綠素和鞭毛體這三種細胞器都曾經是「自由生活的原核細胞」。3 合併原屬不同生物個體的細胞,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順遂。那可能是透過掠食、寄生、侵略或捕捉等。不同的敘事喻說,會講述出不同價值的故事,但幾乎沒有任何敘事是完全確定的。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複雜生命形式都經歷了一連串的重新分配動態。敘事的隱喻可以是美好的共生,也可以強調其中無可避免的力量爭鬥。古生物學家布拉希爾(Martin Brasier)就用「奴役」(enslavement)一詞來形容多細胞藻類的形成。從葉綠體的多重細胞壁可以推論:早期真核細胞「吞沒」藍綠菌,形成有雙重膜葉綠體的藻類,紅藻和綠藻也都是來自這類「奴役」,然後又被不同的真核生物所「吞沒」,產生像有三層膜的棕藻。如此發生多次,內部的共生體在宿主內部逐漸失去重要的基因,終於再也無法「逃脫」。4 奴役的敘事確實映照了資本主義軍事殖民的意識形態,卻也同時和後殖民及抵殖民的界線協商政治有著強烈的共振。
包覆、摺疊、展開和纏繞,在一切環繞彼此的太陽系中,地球生命的巴洛克形構早已經是一種藝術創作,但同時也是無法漠視的界線政治。
二、歷史意識的分子化塗鴉
我們世界的中心確實不斷晃動著,因為整個系統中複雜而大小不一的動力行動者。從肉眼可見的地球或太陽到肉眼不可見的質量中心,反映了我們身為肉身存在物的認知裝置演化。這樣的演化橫跨肉眼科學的直觀與概念,以及組裝配置越來越複雜的延伸認知。系統的概念讓我們看到更大的圖像,同時要求我們去看見更小尺度的過程。從十七世紀末至今成像技術(imaging technology)的快速增生,促成了科學和哲學的分子轉向(molecular turn)。如同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言,我們身處並參與著各種意義的內爆(implosion),包括主體和客體之間,文化和自然之間,生物學和資訊學之間,有機體和機器之間,事實上,各種範疇對立之間。5 各種內爆中的動態生成,也可以理解為巴芮德(Karen Barad)所說的「世界的內動化成」(intra-active becoming),其中的能動參與者(agential participants)包括各種人類和非人類的組裝,及其測量行動。6 拉圖(Bruno Latour)近年來援用地質學中的臨界區(critical zones)、變形區(metamorphic zones)等概念來彰顯不同類屬能動力的重新分配;特定地方的形構並不是既定或設計好的,而是出自異質力量之間無盡的交會和協作,人類行動者之所以必須主動參與「構築共同世界」(composing the common world)的任務,正因為「共同」並非理所當然。7 人與非人的二元區分早已不夠用,我們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明察與行動;但我們早已這麼做,尤其在科學中,但我們仍需要更多的歷史覺察。界線在任何尺度上的跨越與重構都會對其中的能動者產生影響甚或造成風險。
「我們」當然早已不完全是人類,不僅就我們的延伸認知實踐所涉及的跨界組裝性來說,或是以人類基因組的跨物種演化構成來說。我們的基因組中有百分之8是病毒基因序列,稱為「內源逆轉錄病毒序列」(endogenous retroviral sequences),來自於人類和其他靈長類及哺乳類動物共同的深度演化歷史,體現了前人類遠古時期以來的感染、繼承並持續共生演化的跨物種肉身記憶。8 在某種意義上,組裝或混雜的意義橫切了後人類(the posthuman)和前人類(the prehuman)的非線性時序性(nonlinear temporality)。我們從來不僅是人類;我們不再僅是人類。我們正在見證的是,對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兩種解構模式之間的相會。在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困局中,後殖民的混雜意識取得了新的價值,甚至溢出了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面對氣候變遷挑戰時,重新思考歷史所提出的第四命題,「物種歷史和資本歷史的交叉影線是一個探測歷史理解的限度的過程」(The cross-hatching of specie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apital is a process of probing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9 根據基因組研究,後殖民混雜性可以往前追溯到跨物種深度歷史的非線性演化,在此,歷史理解交錯著演化歷程,也就不斷必須改寫它的界線。
「交叉影線」(cross hatching)是素描中常用的加陰影技法,以一支筆就可以畫出明暗(values)、色調(tones)、陰影(shade),透過在較簡單的平行影線(parallel hatching)之上疊加垂直交錯的另一層。倘若我們考慮到前人類綿延到後人類的跨物種或多物種深度歷史,交叉影線的技法雖然好用,卻可能並不是最恰當的。藝術治療中廣泛應用的塗鴉技法(scribbling technique)或許是更具發揮空間的隱喻。塗鴉技法以流動的線條去勾勒出物體的輪廓、事件的展開、形式的纏繞、動態的向度,以及非線性的複數時間性。歷史的理解並不是沒有限制,也不僅是從地方擴展到行星的尺度。正如秦(Anna Tsing)指出,在擴充尺度的過程中一定會碰到無法直接縮放的情況(unscalability)。10 透過當代科學的分子轉向,我們的歷史理解正在不斷重構歷史的語意界線(semantic boundaries)。所有邊界或限制,都在分子層次的視覺化與測量中發生量變與質變。在一世紀前誕生的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正是始於尺度的知識域落差,亦即,當科學家發現,普遍適用於解釋人類直觀日常生活的傳統力學,在次原子的電子尺度上卻頓時失去了解釋力。此一涉及知識及存在的危機至今仍未獲充份解答。11 在我們的時代,分子化塗鴉(molecular scribbling)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歷史意識技術。在非線性的分子演化塗鴉中,生命的跨物種筆觸不僅畫出了混雜、跨界、合併和協同,也在刻畫衝突、拉扯、撕裂,並在生和死的邊界上持續騷動,恰如後殖民政治的生態。比如,以原住民族藝術家的作品為例;倘若看起來太「混種」或「現代」,其文化本真性(cultural authenticity)就會遭遇質疑。其他少數族群的作品也會面對類似質問。當代的非西方藝術家或思想家往往遭遇類似困境。在高技術資本主義時代,各種物質及記號元素都在持續流動並混雜著,但某些主體依然承受非普遍的標記,她們必須在雜揉處境中更用力地標記出自身的主體性。
後殖民的分子化塗鴉不應該抹滅界線;反之,必須在纏繞之中勾勒出界線,無論有多暫定。在跨物種、多物種、物種間的複雜勾連中,如何標示出物種歧視的毀滅後果,是後人類生態政治的核心任務。在工業化農場的時代,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形同提出了一種阿圖賽式的意識形態詢問(Althusserian ideological interpellation),我們無法再迴避病毒所具現化的跨物種生命政治(trans-species zoopolitics)。後殖民的族群和文化戰爭,早已在席娃(Vandana Shiva)所說的「哥倫布再臨」(Second Coming of Columbus)中,蔓延到非人類世界。12 在階級、性別、族裔、物種等界線的交叉影線中,分子化塗鴉的筆觸也延展到深度歷史和遙遠未來。由於分子層次的成像技術,人類不能不去看見自身和其他生命形式在這座行星上的演化糾纏,也不得不持續去跨越藝術和科學之間的界線。在二十一世紀,當代藝術,如同當代科學,必須參與對於一切界線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all boundaries)。


從一名患者身上分離出的SARS-CoV-2病毒顆粒的透射電子顯微照片。圖像由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NIAID綜合研究設施(IRF)進行擷取與色彩優化。圖片來源:NIAID∕CC BY 2.0
三、分裂的尺度以及旅行的意義
每個時代都是分裂的,而我們的分裂既是分子化的,也是行星尺度的。借助延伸認知的裝置,我們現在可以運用螢光分子DNA感應器去探查並視覺化細胞受體的力學反應;我們也可把地球改裝成一座行星尺寸的天文望遠鏡,去觀測並拍攝距離地球有五千五百萬光年的黑洞,宇宙中巨大的熵(entropy)或混亂。13 然而,我們依然未能充分紀錄並理解地球豐富的生物多樣性,也無法協調人類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與衝突,更難以判斷社會政治中混亂的根源。我們看不清自己的樣貌,也無能碰觸自己的心靈。人類世在知識論與倫理學上的曖昧正在於,人類認知裝置與科技圈的膨脹製造了生命多樣性的危機,但也一再迫使人類去面對自己的混雜、依賴與脆弱性。與此相關的政治弔詭則是,只能生活在同一座行星上的我們,卻分崩離析,失去或從未獲得構築共同世界的能力。
在Covid-19的時代,病毒的能動形象(agential image)意外成為這個分裂世界中的一種溝通方式。不過,同時凸顯了原本就存在的各種不平等與隔閡。或許這座行星從不屬於我們,這是一座病毒的行星。在前人類和後人類之間勾連的非線性迴圈,病毒始終在不同物種之間持續進行交叉影線和分子塗鴉的時空繪製,勾勒其中的界線。病毒是地球上最傑出的寄生者,也是我們時代最確實的隱喻。我們藉此共享的跨物種存有論充滿後果。寄生與共生之間交織難解的複雜關係,發生在生命從最小到最大的各種尺度上。這早已超出了傳統上所說的食物鏈意象,其傾向於強調獨立個體之間的掠食關係,更多是隱約、遮蔽、幽暗、秘密、難以窺見的情報作戰與複雜連結,不斷改寫著內外的界線,形成更複雜的分子訊息演化網絡。共生和寄生在人類生活世界語言中被分別賦予的善惡道德意象也受到了挑戰,事實上,兩者的界線從未分明。借助當代的視覺化和測量技術,我們得以觀察到特定微型界線的動態協商,無不持續重塑了我們對於生物個體性(biological individuality)的理解,亦即所謂自我和他者的分界。各種生命形式,包括以往不被視為生命或被視為缺乏獨立性的形式,都在不同尺度的演化事件中形成共生、寄生、合生的反饋迴圈,以及訊息共享的延伸系統。
當我們在國族、社會、政治及文化的尺度上呈現斷裂的狀態,在病毒和微生物的尺度上卻早已有著分子層次的演化糾纏,在行星的層次上則始終不停歇地一起旋轉。斷裂、糾纏、旋轉,這些都是我們活著的動態,充滿危險,但也蘊含未來的種子。病毒和行星所具有共同點在於演化的歷史與軌跡。事實上,這個特點也適用於不僅是人類的我們,身為這座行星上的生命形式,所必須面對的最根本現實。我們的現實是能動的(agential),但同時也承載著複數時序性的歷史重量。
一切始於我們對自己的追求,但我們唯有透過尋找他者才能看見自己。我們的行星也是如此。蓋婭的理論始於人類探索何以這座行星可以支持生命的形成,隨即發現生命一旦出現就開始了分子層次的纏繞塗鴉,並促成這座行星的生命進一步演化。但有時候,遙遠時空的迷濛「他者」形象,遮掩了此時此地的生活。從上個世紀中至今,科幻影視中源源不絕的星際探索和賽伯格意象,洩露了這樣的潛意識換置。克萊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克萊恩( Nathan S. Kline)在1960年一篇關於如何讓人類得以去探索太空的文章中發明了「賽伯格」(cyborg)一詞。他們用了一個傳神的比喻:如果一隻魚想在陸地上生活呢?它無法。但若這是一隻高智能,精通生物學、工程學和模控學的魚呢?它會知道,它必須延伸自己的有機體控制系統,將其組裝到一個模擬棲居地的控制系統。換言之,它必須把自己賴以為生的水棲地帶在身上,成為它的延伸物;它必須成為一個模控有機體(cybernetic organism),也就是賽伯格。14 這樣的必然乃是建立在我們身心結構的演化歷史上,無論你是人,是魚,或其他生命形式。歷史性讓遷移和旅行成為一種壓力源,因為就連你身體的內部及外部壓力也都是有歷史的。
到太空旅行的人類,如果要存活,必須把自己的行星背在身上,成為這隻個別有機體的延伸裝置。更精確來說,她本身必須成為一座移動的迷你行星。這座迷你行星的模型不能是任何其他行星,這座行星必須擁有讓她得以在其中演化與茁壯的獨特生命圈,包含足以維持生命的種種生物化學條件和複雜的反饋迴圈,亦即蓋婭。就像哈洛威所言,「飛往外太空的賽伯格就像是小型的、自我維持的蓋婭」(Space-bound cyborgs were like miniaturized, self-contained Gaias)。15 重點是,這樣的小型蓋婭可以自我維持多久?就像地球,作為一個有生命棲息的行星,倘若脫離環繞太陽的軌道,飛往奇異的外太空,它的生命圈,在失去主要的外部能源的情況下,可以維持多久?
尋找另一座可以棲居的行星,亦即地球的另一個自我(alter ego),這樣的追求同時發生在科學、藝術、文學等場域當中。從1990年代中開始,科學家陸續發現了我們太陽系以外,環繞其他發熱星球的行星,稱為系外行星(exoplanet)。而今我們知道這些行星無所不在。我們知道,因為我們「看過」其中一些。透過我們的延伸感官裝置,去視覺化、測量、紀錄與分析,並讓我們的記憶、概念和意識都沈浸在這些龐大的資料和影像中。這些做法豐富了我們的想像,但也可能餵養了我們的逃避症狀。或許,我們的潛意識已經準備好,隨時可以放棄地球這個自我,奔向另一個「超級可棲居的」(superhabitable)行星,另一個在想像中等著被發現的更好地球。16
此外,科學家又發現宇宙中有大量流浪的行星,它們沒有環繞任何星球,也不太可能演化出生命。它們是偏離軌道的,或被拋棄的行星,或是誕生在沒有母星的氣體與塵埃中的孤兒行星。科學家稱呼它們為「流浪行星」(rogue planets)。這些流浪的世界也許是宇宙中最孤獨的黑暗旅行者,它們是自己的家,卻很難成為生命的家。它們很難被偵測到,因為基本上沒有光源。透過人類延伸到太空的感官裝置,此處是指預計在2025年興建完成的羅曼太空望遠鏡(Nancy Grace Roman Space Telescope),我們將可間接觀察到流浪行星:當它們恰好和遠方發光星球排列成一直線時,通常維持大概幾個小時或數天(地球時間),就可以從行星質量所造成的時間空間彎曲,以及隨之產生的光子運動變化,去推斷這顆流浪行星的大小。17 身為觀察者,我們人類從未如此忙碌。我們正在密切觀察新冠病毒刺突和人類細胞受體之間的互動,我們正在以行星大小的望遠鏡紀錄遙遠的黑洞。而今,我們準備利用遙遠天體之間的物理關係來觀察流浪的行星。一切生命存在物都是觀察者,在其棲地上測量與改造。人類身為觀察者的測量體制正在不斷膨脹,看得更小,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看得更大。我們迷失在中間,在最廣闊和最微小的尺度之間。對人類來說,中間總是太平庸,而日常過於繁瑣,此時此地則是所有迷惘的質心。
誠如拉圖的提醒,「 如果你不說自己想在哪裡定居,你就無法問你可以在哪裡定居」(you cannot ask where you can settle if you do not say where you yourself wish to settle.)18 更急迫的問題或許是,你必須帶著什麼去到哪裡生活。我們並不屬於一個地方,地方也不屬於我們。但在我們移動時,總是攜帶著我們的地方,不自覺地。無論我們旅行到何處,我們攜帶著,我們的歷史,我們的記憶,我們的島嶼,我們的行星,以及我們共同及個別演化出來的延伸感官與文化裝置。
很可惜,但也幸好,我們只能和彼此一起生活在某種中介尺度上,那既是人的也不僅是人的尺度。我們是混雜了分子和行星的多重尺度存在物。如此複雜的存在只能活在一個多重中介尺度的生活世界裡。在人類最狂野的身心延伸中,我們想像,即使失去肉身,我們也可以繼續觀察、測量、感受,愛與記憶。人類渴望去流浪,因為還有一個行星的家可以回,這個家叫做地球。就像你的靈魂偶而想像離開身體,只因你以為還有一個肉身的家可以回。在行星尺度的觀測時代中,最大的悖論在於,我們可以看見其他行星在流浪,卻看不見自己行星上的流離失所。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行星相對於地球的軌道傾角,卻完全不了解我們的社會、政治與文化軌道有多偏差。一座行星只能生活在它誕生與演化的太陽系中,恰如我們只能生活在這座行星上的特定棲地裡。我們是著地的存在物。
我們的地方,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進步的;它是分子的,也是行星的,以及中間的;它是關於生命與技術,也是關於藝術和政治。在我們不僅是人類的非線性演化中,滿溢著發自無數體現觀點的分子塗鴉:做出空間、時間和物質的藝術,以及共乘、分離、碰撞和密會的軌道政治。棲居於這樣的生活世界,在所有尺度的無盡鬥爭中,我們會在中途相遇嗎?
NASA Science, “What Is a Barycenter?” NASA Space Place, June 3, 2020 →.
Lynn Margulis and James E. Lovelock, “Biological Modulation of the Earth’s Atmosphere,” Icarus 21, no. 4 (1974): 471–89.
Lynn Margulis and Dorion Sagan, What is Life?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Martin Brasier, Secret Chambers: The Inside Story of Cells and Complex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0.
Donna Haraway, The Haraway Reader (Routledge, 2004).
Karen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7.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Polity Press, 2017). Latour, “Some Advantages of the Notion of ‘Critical Zone’ for Geopolitics,” Procedia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no. 10 (2014): 3–6.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35, no. 2 (2009): 220.
Anna Lowenhaupt Tsing, “On Nonscalability: The Living World Is Not Amenable to Precision-Nested Scales,” Common Knowledge 18, no. 3 (2012): 505–24.
Roger Penrose, The Large, the Small and the Human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Vandana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South End Press, 1997).
Joshua M. Brockman et al., “Live-Cell Super-Resolved PAINT Imaging of Piconewton Cellular Traction Forces.” Nature Methods 17, no. 10 (2020): 1018–24. Davide Castelvecchi, “Black hole pictured for first time—in spectacular detail,” Nature 568, no. 7752 (2019): 284–85.
Manfred E. Clynes and Nathan S. Kline, “Cyborgs and Space,” Astronautics, September 1960.
Donna Haraway, “Cyborgs and Symbionts: Living Together in the New World Order,” in The Cyborg Handbook, ed. Chris Hables Gray with Steven Mentor and Heidi J. Figueroa-Sarriera (Routledge, 1995), xv.
Dirk Schulze-Makuch et al., “In Search for a Planet Better than Earth: Top Contenders for a Superhabitable World,” Astrobiology, September 18, 2020.
Ashley Balzer, “Unveiling Rogue Planets with NASA’s Roman Space Telescope,” NASA, August 21, 2020 →.
Subject
翻譯:張君玫